伤寒论名家解读汇编——第34条
 四川-海天 推荐
四川-海天 推荐 四川-海天 已点赞
四川-海天 已点赞注:1、以下是历代名家对伤寒论解读观点的出处索引,可以为大家对比阅读提供参考;2、因时代不同作者所引用的伤寒论版本差异,整理遗失等客观原因,部分条文解读或有缺失敬请谅解!

第34条:太阳病,桂枝证,医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黄芩黄连汤主之。
成无己《注解伤寒论》
太阳病,桂枝证,医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黄芩黄连汤主之。
经曰:不宜下,而便攻之,内虚热入,协热遂利。桂枝证者,邪在表也,而反下之,虚其肠胃,为热所乘,遂利不止。邪在表则见阳脉,邪在里则见阴脉。下利脉微迟,邪在里也。促为阳盛,虽下利而脉促者,知表未解也。病有汗出而喘者,为自汗出而喘也,即邪气外甚所致。喘而汗出者,为因喘而汗出也,即里热气逆所致,与葛根黄苓黄连汤,散表邪、除里热。
葛根黄芩黄连汤方
葛根半斤甘草二两黄芩二两,味苦寒黄连三两味苦寒
《内经》曰:甘发散为阳。表未解者,散以葛根、甘草之甘苦;以坚里气弱着,坚以黄芩、黄连之苦。
上四味,以水八升,先煮葛根,减二升,内诸药,煮取二升,去滓。分温再服。
方有执《伤寒论条辨》
太阳病,桂枝证,医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黄芩黄连汤主之。
葛根黄芩黄连汤方
葛根半斤甘草二两黄芩三两黄连三两
上四味,以水八升,先煮葛根,减二升,内诸药,煮取二升,去滓,分温再服。
此与上条因同而变异。利遂不止以上,与上条上节,两相更互发明之词;脉促以下,言变殊,故治异也。促为阳邪上盛,阳主表故为表未解之诊。喘汗者,里虚阴弱而表阳不为之固护也。夫表未解而利则属胃,有阳明之分也。故肌之当解者,从葛根以解之。以喘汗不独表实而有里虚也,故但从中治而用甘草以和之。然利与上条同,而上条用理中者,以痞硬也。此用苓连者,以喘汗属热为多也。然则四物之为用,其名虽与上条殊,其实两解表里则一耳。
喻嘉言《尚论篇》
太阳病,桂枝证,医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黄芩黄连汤主之。
太阳病,原无里证,但当用桂枝解外。若当用不用而反下之,利遂不止,则热邪之在太阳者,未传阳明之经,已入阳明之府。所以其脉促急,其汗外越,其气上奔则喘,下奔则泄,故舍桂枝而用葛根,专主阳明之表,加芩、连以清里热,则不治喘而喘自止,不治利而利自止,又太阳两解表里之变法也。不解肌,反误下,宜辨阳实阳虚,加减桂枝汤一法。
张志聪《伤寒论集注》
太阳病,桂枝证,医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黄芩黄连汤主之。
葛根黄芩黄连汤方
葛根半斤甘草二两黄芩三两黄连三两
上四味,以水八升,先煮葛根,减二升,内诸药,煮取二升,去滓,分温再服。
高子曰;”上三节乃太阳经脉之从上而下者,复可从下而上;此言太阳肌腠之从外而内者,亦可从内而外也。”太阳病桂枝证者,病太阳之气而涉于肌腠也。医反下之,则妄伤其中土,以致利遂不止。脉促者,太阳阳气外呈,不与里阴相接,故曰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乃肌腠之邪欲出于表,故宜葛根黄芩黄连汤主之。葛根、甘草从中土而宣达太阳之气于肌表,黄芩、黄连清里热而达肺气于皮毛。
张锡驹《伤寒论直解》
太阳病,桂枝证,医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黄芩黄连汤主之。
葛根黄芩黄连汤方
葛根半斤甘草二两黄芩三两黄连三两
上四味,以水八升,先煮葛根,减二升,内诸药,煮取二升,去滓,分温再服。
【注】太阳病桂枝症,病在肌也,医反下之,由肌而内陷于中土矣,无故而殒,所以利遂不止也;脉促者,邪虽内陷而气仍欲外出,此表尚未解也;喘作汗出者,邪欲从肌腠而外出于表,一时不能外达,故作喘;肺主皮毛,喘则皮毛开发,故汗出。葛根黄芩达太阳之气于外,黄连清陷里之邪热,甘草所以补中也。
愚按:下后发喘汗出,乃天气不降,地气不升之危症,宜用人参四逆辈,仲师用葛根黄芩黄连者,专在表未解一句。虽然,仲师之书,岂可以形迹求之耶?总以见太阳之气出入于外内,由外而入者,亦可由内而出,此立症立方之意也。
尤在泾《伤寒贯珠集》
太阳病,桂枝证,医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黄芩黄连汤主之。
太阳中风发热,本当桂枝解表,而反下之,里虚邪入,利遂不止。其脉则促,其证则喘而汗出。夫促为阳盛,脉促者,知表未解也。无汗而喘为寒在表;喘而汗出,为热在里也。是其邪陷于里者十之七,而留于表者十之三,其病为表里并受之病,故其法亦宜表里两解之法。葛根黄连黄芩汤,葛根解肌于表,芩、连清热于里,甘草则合表里而并和之耳。盖风邪初中,病为在表,一入于里,则变为热矣。故治表者,必以葛根之辛凉;治里者,必以芩、连之苦寒也。而古法汗者不以偶,下者不以奇。故葛根之表,则数多而独行。苓、连之里,则数少而并须。仲景矩镬,秩然不紊如此。
葛根黄芩黄连汤方
葛根半斤甘草二两黄芩三两黄连三两
上四味,以水八升,先煮葛根减二升,纳诸药,煮取二升,去滓,分温再服。
柯琴《伤寒来苏集》
太阳病,桂枝证,医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黄芩黄连汤主之。
桂枝症上复冠太阳,见诸经皆有桂枝症,是桂枝不独为太阳设矣。葛根岂独为阳明药乎?桂枝症,脉本弱,误下后而反促者,阳气重故也。邪束于表,阳扰于内,故喘而汗出。利遂不止者,所谓”暴注下迫,皆属于热”,与脉弱而协热下利不同。此微热在表,而大热入里,固非桂枝芍药所能和,厚朴、杏仁所宜加矣。故君葛根之轻清以解肌,佐连苓之苦寒以清里,甘草之甘平以和中,喘自除而利自止,脉自舒而表自解,与补中逐邪之法迥别。上条脉症是阳虚;此条脉症是阳盛。上条表热里寒;此条表里俱热。上条表里俱虚;此条表里俱实。同一协热利,同是表里不解,而寒热虚实攻补不同。补中亦能解表,亦能除痞;寒中亦能解表,亦能止利。神化极矣。
吴谦《医宗金鉴》
太阳病,桂枝证,医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黄芩黄连汤主之。
〔注〕此承上条又言协热利之脉促者,以别其治也。太阳病桂枝证,宜以桂枝解肌,而医反下之,利遂不止者,是误下,遂协表热陷入而利不止也。若表未解,而脉缓无力,即有下利而喘之里证,法当从桂枝人参汤以治利,或从桂枝加杏子厚朴汤,以治喘矣。今下利不止,脉促有力,汗出而喘,表虽未解,而不恶寒,是热已陷阳明,即有桂枝之表,亦当从葛根黄芩黄连汤主治也。方中四倍葛根以为君,芩、连、甘草为之佐,其意专解阳明之肌表,兼清胃中之里热,此清解中兼解表里法也。若脉沉迟,或脉微弱,则为里寒且虚,又当用理中汤加桂枝矣。于此可见上条之协热利,利不止,心下痞硬,表里不解者,脉不微弱,必沉迟也。
〔按〕协热利二证,以脉之阴阳分虚实,主治固当矣。然不可不辨其下利之粘秽、鸭溏,小便或白或赤,脉之有力无力也。
〔集注〕成无己曰:病有汗出而喘者,谓自汗出而喘也,是邪气外甚所致。若喘而汗出者,谓因喘而汗出也,是里热气逆所致,故与葛根黄芩黄连汤,散表邪除里热也。方有执曰:利与上条同。而上条用理中者,以痞硬、脉弱属寒也。此用芩、连者,以喘汗、脉促属热也。喻昌曰:太阳病,原无下法,当用桂枝解外,医反下之,则邪热之在太阳者,未传阳明之表,已入阳明之里。所以其脉促急,其汗外越,其热上奔则喘,下奔则泄,故舍桂枝而用葛根,以专主阳明之表,加芩、连以清里热,则不治喘而喘止,不治利而利止。此又太阳、阳明两解表里之变法也。
汪琥曰:误下虚其肠胃,为热所乘,遂利不止,此非肠胃真虚证,乃胃有邪热,下通于肠而作泄也。脉促者,脉来数时一止复来也,此为阳独盛之脉也。脉促见阳,知表未解,此表乃阳明经病,非犹太阳桂枝之表证也。喘而汗出者,亦阳明胃腑里热气逆所致,非太阳风邪气壅之喘,亦非桂枝汤汗出之证也。故当解阳明表邪,清胃腑里热也。
陈修园《伤寒论浅注》
太阳病,桂枝证,医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黄芩黄连汤主之。
【注】太阳病,头项强痛,自汗,恶风,为桂枝证,病在肌也。医反下之,致太阳之邪由肌而内陷,利遂不止。
然邪虽内陷而气仍欲外出,其脉急数中时见一止而无定数,其名促。脉促者,表邪未能迳出而解也。
邪欲出而未能迳出则喘,喘则皮毛开发而汗出者,此桂枝证误治之变。既变则宜从变以救之,不可再用桂枝汤,而以葛根黄芩黄连汤主之。
此一节,言太阳证虽已陷邪,亦可以乘机而施升发,使内者外之、陷者举之之妙也。
张令韶云:下后发喘汗出,乃天气不降、地而不升之危证,宜用人参四逆辈。
仲师用此方,专在”表未解”句。虽然仲师之书。岂可以形迹求之耶?总以见太阳之气出入于外内,由外而入者亦可由内而出,此立证立方之意也。
陈伯坛《读过伤寒论》
太阳病,桂枝证,医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黄芩黄连汤主之。
本条太阳阳明尚合病否乎?不合病之合病,不分病之分病,邪则分而正则合。一邪分作两邪,两阳合为一阳,皆下药为之厉也。书太阳病,明明阳明不病矣。书桂枝证,阳明宜桂仅两见,太阳主桂则屡矣。奈何医反下之?劈分桂枝证为两面病,一面干动阳明署之里,反逼阳明合太阳。一面占据太阳署之表,反逼太阳合阳明。两阳相参错,岂独合而不离已哉?直藏阳明于太阳病形之里,桂枝证又从而掩之,非掩以初得病时之外证也。下后不得复有外证,己翻作太阳病在表,阳明病在里矣。则可见而不可见者,半为热邪薄于表,不可见而可见者,半为热邪薄于里也。书利遂不止,非里证乎哉?看似阳明较为吃亏,不知两阳皆桎梏于热邪交迫之夹缝,欲合任其病而不得,欲分任其病而不能,其为无开阖之余地则一也,殆葛根证之变者欤?再征诸脉,若两阳之阳,不甘逼处而现数状,不能不受逼处而时或不数状。两阳之阴,愈受逼处而现止状,不尽逼处而时或一止状,是谓促脉,在桂枝证度亦外未解焉已。曰表未解也,里未解不待言。如欲以解外法解表,乌能以解外法解里乎?况喘而汗出,与桂枝加厚朴杏子证显有异同乎?勿见其汗出不恶寒,认为表已解也。乃表热牵其里,里热牵其表,正惟未欲解而后迫为汗,故不出太阳受病之汗,转出阳明似病非病之汗也不然,却发热汗出而解矣何至喘而汗出,不喘便无汗岀乎?且凡太阳病欲解时,曷尝以喘得汗乎?假令汗出而喘又何若?彼证之汗,非不足以却邪,特梗阻其汗者喘。本证之汗,实不足以却邪,徒发动其喘者汗。彼证汗而喘,不可更行桂枝汤。本证喘而汗,误在不先行桂枝汤也。虽然,初不过错过一桂枝证耳,变端何至若是?误下者尚有辞以解嘲也。惟与医者约,许其追认桂枝证以易方,开阖两阳,肃清表里,彼将托故而去矣,盖恐其宜服四逆辈也。曰葛根黄芩黄连汤主之,何其闲视利遂不止乎?方旨详注于后。本汤又君葛矣,易方不易葛,何需葛之殷乎?前路器重葛,犹乎后路器重柴。葛根打入太阴作用,柴胡打入少阳作用,皆足匡麻桂之不逮,要以葛根为功首。盖有柴在,能令太少不相失。有葛在,愈见阴阳相互根也。且柴胡无加连之例,葛根则并芩连而左右之,宜乎桂枝证以加葛为前提,本证则特立葛为中坚也。方内鼎足其药者三,而先煮一味如奇偶。葛根固让功于芩连,芩连实效力于葛根。芩解表,连解里,表热里热不得逞,葛根遂起阴气以开阖其两阳,再服则三味之能事已毕,非斤斤于止利止喘止汗为也。独是命方曰葛曰芩曰连而不曰草,岂以其无足轻重而漏之耶?是又一味让功于三味,甘草非用以和药气,盖用以和病形。病形以不治治之,甘草不必有其德也。何以利不止亦热耶?得毋作协热利耶?非也。并于阳则热,形下不热形上热。促脉其明征,喘汗其明征也。其所以利不止者,以利滑之药力犹存在,药尽利遂止,未尽遂不止。止不止操在庸医之手,非因下利之故遂如是,亦非自利之故遂如是。谓为下利不得,谓为自利不得,但利而已。所具各证,乃下药造成有形之病,掩却无形之证。本方是针对无形之桂枝证,非针对有形之太阳病也。不以桂枝汤治桂枝证,而代桂以葛。总结上文一路变通桂枝汤,自加葛始也。葛根此后不再见,葛与桂相终始,又起下桂与麻若离合也。
曹颖甫《伤寒发微》
太阳病,桂枝证,医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黄芩黄连汤主之。
葛根黄芩黄连汤方
葛根半斤甘草二两黄芩三两黄连三两
上四味,以水八升,先煮葛根减二升,纳诸药,煮取二升,去滓,分温再服。
此节”医反下之”至”表未解也”为一证,”喘而汗出者”为又一证。太阳魄汗未尽,误下者利不止,此与内陷之自利,略无差别。但仲师于此节郑重分明,历来为注释家所误。未能分析,致仲师立言本旨,如堕五里雾中。今特为分析言之。仲师曰:脉促者,表未解也。表属皮毛,皮毛未解,固不宜专用解肌之桂枝汤。脉促,即浮紧之变文,曰”表未解”,则仍为葛根汤证,与上”自下利”证同法,不言可知。惟喘而汗出,则阳热内盛,里阴外泄,乃为葛根芩连汤证。其作用正在清热而升陷,注家含糊读过,妄谓喘而汗出,即上所谓表未解,夫岂有表未解而汗出者乎?
恽铁樵《伤寒论辑义按》
太阳病,桂枝证,医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黄芩黄连汤主之。原注:促,一作”纵”。
成无己云:桂枝证者,邪在表也,而反下之,虚其肠胃,为热所乘,遂利不止。邪在表则见阳脉,邪在里则见阴脉。下利脉微迟,邪在里也。促为阳盛,虽下利而脉促者,知表未解也。病有汗出而喘者,为自汗出而喘也,即邪气外甚所致。喘而出汗者,为因喘汗出也,即里热气逆所致。与葛根黄芩黄连汤,散表邪除里热。汪琥云:成注”虚其肠胃”,此非肠胃真虚证,乃胃有邪热,下通于肠,而作泄也。
钱璜云:促为阳盛,下利则脉不应促。以阳邪炽盛,故脉加急促,是以知其邪尚在表而未解也,然未若协热下利之表里俱不解。及阳虚下陷,阴邪上结,而心下痞硬,故但言表而不言里也。
柯韵伯云:邪束于表,阳扰于内,故喘而汗出。利遂不止者,所谓”暴注下迫,皆属于热”,与脉弱而协热下利不同。此微热在表,而大热入里,固非桂枝、芍药所能和,厚朴、杏仁所宜加矣。
《医宗金鉴》云:协热利二证,以脉之阴阳,分虚实主治,固当矣。然不可不辨其下利之黏秽鸭溏,小便或白或赤,脉之有力无力也。
张锡驹:下后发喘汗出,乃天气不降,地气不升之危证,宜用人参四逆辈。仲景用葛根黄芩黄连者,专在”表未解”一句。
《伤寒类方》曰:促有数意,邪犹在外,尚未陷入三阴而见沉微等证象,故不用理中等法。
铁樵按:葛根芩连汤,乃常用之药,如各注家说,几令人弥所适从。近人畏葛根,谓是升药不可用;畏芩连,谓是苦寒不可用。于是乞灵于豆卷。当表不表,病则传里,壮热而渴,更乞灵于石斛。病毒为甘凉遏抑,不能从汗解,因出白㾦。从此节节与《温病条辨》相合,《伤寒论》乃束之高阁。又岂知用药一误,病型随变。此真千古索解人不得之事也。葛根之升,乃从肌腠升于肌表之谓,非从下上升之谓。病人往往先告医生,谓我向有肝阳,请先生勿用柴胡、葛根。或者病已退热,头或微晕,则归咎于柴胡、葛根。其有服解肌药未即退热者,改延他医,则必大骂柴胡、葛根,而恣用石斛。病延至三候,无险不呈,病家终不知所以致此之由。则因时医手笔皆出一辙,彼此互相回护故也。此真举国皆饮狂泉,转以不狂者为狂之类。而西医习与此辈较短长,反以为中国医术,不过尔尔,令人为仲景呼冤不置。
详”脉促者,表未解也”两语,意思颇深。脉促,即促结代之促,脉搏有歇止者是也。脉所以促,正因下之不当,下之太骤之故。脉之跳动因心房之弛张,其弛张最有程序。苟非脉管栓塞,闭锁不全,脉搏断不至有歇止。然当表邪未解,正气未衰,误用泻药,邪欲陷而不得,欲出而不能,互相格拒脉管中,神经因感非常剧变,弛张顿失常态,其气遂乱,脉乃见歇止。此是促脉之真相。然何以云”表未解”也?此句委实是”表未陷也”之变词。何以知之?假使表邪随泻药而陷里,则成为结胸,或痞硬,或热结上膈。凡如此者,其脉不促。既非因心病即血病。或肝病即神经过敏病。二者均详后。而脉促,此促脉乃暂局,下药太暴,邪正互争,脉气因乱故也。既如此,邪之内陷者不得入里,势必还归于表,因此知表未解。故云”表未解”句是表未陷之变词。”喘而汗出者”一句,亦千古无人解得。须知此节之文字,当云”太阳病,医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葛根汤主之。喘而汗出者,表已解也,葛根黄芩黄连汤主之”。何以知之?表未解当用表药,伤寒之定例。凡言表、言汗,皆指麻黄。其桂枝、葛根,只是解肌药,不名为表,故知”表未解”之下,当接葛根汤主之。葛根汤,有麻黄者也。内陷有寒、有实、有热。喘而汗出者,热结上膈。何以知是热?以用芩连知之。即证可以知药,即药可以知病,亦伤寒之例。故舒驰远谓”喘而汗出,当用人参四逆辈”,张锡驹谓”是天气不降,地气不升”,真是梦呓,丝毫不曾理会得《伤寒》读法。喘而汗出,是表已解。何以知表已解?因”汗出”字知之。观”无汗而喘,麻黄汤主之”,即知无汗是表不解,因而推知有汗是表已解。又因而推知,”表未解”之”未”字,正对表已解说。惟其如此,省去一句,读者可以自明,否则不能省也。故知”喘而汗出”之下,有”表已解也”一句。
余既解释此节,三复之,觉有至理,非如此不可,且亦甚平正,一望而可知者。不料成无己以下诸注家言人人殊,只是搔不着痒处。诸公之拙,当为仲景所不料。
葛根黄芩黄连汤方《千金》《外台》作”葛根黄连汤”
葛根半斤甘草二两,炙黄芩三两黄连三两
上四味,以水八升,先煮葛根,减二升,纳诸药,煮取二升,去滓,分温再服。
柯韵伯云:君气轻质重之葛根,以解肌而止利;佐苦寒清肃之芩、连,以止汗而除喘;用甘草以和中。先煮葛根,后纳诸药,解肌之力优,而清中之气锐,又与补中逐邪之法迥殊矣。
《古方选注》云:是方即泻心汤之变。治表寒里热,其义重在芩、连,肃清里热也。
《伤寒类方》云:因表未解,故用葛根;因喘汗而利,故用芩、连之苦,以泄之坚之;芩、连、甘草,为治痢之主药。
冉雪峰《冉注伤寒论》
太阳病,桂枝证,医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黄芩黄连汤主之。
冉雪峰曰:此条系连类而及,推广葛根的功用。葛根证,桂枝麻黄二系均有,故各各分见于论列桂枝证,论列麻黄证里面。但桂枝系的桂枝加葛根汤,麻黄系的葛根汤、葛根加半夏汤,均有姜枣,有麻桂,均是为疗风寒设法。本条不惟无麻桂,并无姜枣,纯脱诸葛根组织制剂范围,变辛温为苦寒,变侧重治外,为内外兼治,诚为太阳两解表里的变局。前诸葛根汤,葛根系用四两,此方葛根系用八两。本条当着眼的在利不止,不止是邪陷,升陷不能不重用葛根。当着眼的在表未解,表未解,适值这个利不止状况下,更不能不重用葛根。就方制说,上诸葛根汤内有麻桂,有姜枣,故葛根只用四两,得辛温促助,输转外透力量已大。此方复味苓连,苦寒沉降,若葛根仍只用四两,其何以济?故加倍成八两,冀挽此颓废败坏的趋势,总之此项方剂意义,为表里双解,了无疑义。而近人必谓此方是治表已解,并谓喘而汗出下,当有表已解也句,不惟改字训经,且添句训经。试问表已解,葛根何必用八两,真是瞽谈。查康平古本,原文系太阳病,医反下之,利遂不止,喘而汗出者,葛根黄连黄芩汤主之。其脉促者表未解也七字,为利遂不止侧面小字旁注,利遂不止,俨似理中辈及桂枝加人参证,不知谁何,在这个脉证矛盾处,寻出真理,颖悟超超。因在利遂不止句,加此小字旁注,如画龙点睛,实可惊异,乃后人反在这个宝贵处生出支节,即将此七字列入正文,又从此句反面,拟在喘而汗出下,加表已解也四字,愈错愈远,抹煞古人精义,汩没后人灵机,曷胜惋惜。学者须知此方应用颇广,凡外证而兼里热,里热而加外证,均可借用。为之一下转语曰:此为太阳两解表里的变法,亦即是其他热病两解表里的证法。
冉氏又曰:太阳与阳明相递接,太阳不解,即传阳明。太阳阳明合病,必自下利,是不俟次内传阳明经的部分,即越次内传阳明府的部分。诸葛根汤,即是升陷转枢,使不内搏内传意思。是太阳不解,其病机自身,原有内陷下利趋势,治疗的精神,即是由外而搏于内者,仍由内而输于外。若误以为病的机窍在内而下之,是促之陷而益其疾,利遂不止,理固宜然。此时首先在看表的罢未罢,若罢,已构成里证,即当从里救治,理中辈桂枝人参汤等条,即是好例子。其次在看化热未化热,未化热,宜诸葛根汤,已化热,宜本条葛根黄芩黄连汤。再其次看在上焦,在中焦,在气分,在血分,变动很繁多,关系很复杂,即辨晰很细致。促原是坏脉,而显出正气伸张力来;喘原是坏证,而显出正气冲激力来。尤寓深邃的奥义。喘而汗出,本太阳病范围常有证象,而在下后的阶段,在下之利不止的阶段,则显出特殊意义。又如麻杏甘石汤,就有无汗而喘,有汗而喘,两个病型,都是表未解。诸葛根汤,亦有反汗出,和无汗,两个病型,亦都是表未解。盖出汗是解表的方法,而汗出并不是表解的定范。喘是气能上冲,汗是气能外达,这就是说明利虽未止,气不全陷的表现,也就是说明表未解的实际象征。再证之前二十二条脉促,后四十三条证喘,均是表未解,通体可以透彻。总上以观,葛根的转输,可以解表,可以和里,可以同热药用,可以同寒药用。可以和表者,连同和里。可以治寒者,变换治热。神而明之,使自宜之,活用原则,存乎其人。
胡希恕《胡希恕伤寒论讲座》
太阳病,桂枝证,医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黄芩黄连汤主之。
太阳病,本来是桂枝证,你看这个书,它提出个”桂枝证”,桂枝证是什么呢?桂枝汤证。所以这个书里头,一个方剂的应用,它有一定的适用范围,这就是某个方剂的适应证,就叫作某方剂之证,简言之,比如桂枝汤证就是桂枝汤的适应证。什么适应证?我们前面讲了,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这类病就应该用桂枝汤。太阳病本来是桂枝汤证,就是发热、汗出、恶风这类的太阳病,那么治病的这个大夫,不知用桂枝汤,而反用下法,给吃泻药,这错了。一吃泻药,他里边本来没病,一吃泻药里边就虚了,那么外边这个外邪乘虚就进里头去了,所以就发生”利遂不止”。这个外邪就是热邪,古人管这叫”协热利”。协同下药,热协同下药而作下利不止,这叫”协热利”。那么这是误治造成的,由于误治不但造成协热利,利遂不止,同时表也没解,所以脉促。
脉促咱们讲过了,这是寸脉促,《金匮要略》上有”脉浮在前,其病在表”。表证的时候,关以前的脉是要浮的。所以咱们上次讲了,促脉,它又迫近于上又迫近于外,就是寸脉独浮这种脉。那么现在脉促,这证明表还没解。它误治了,本来应该用桂枝汤汗以解之,这个大夫给吃泻药,一方面引邪入里而下利不止,另一方面表也未解,所以脉现促。
”喘而汗出者”,这是表里俱热,热呀,凡是热都往上,热涌于上,所以人要喘。汗出有两个问题,一个是里头热也使他出汗,一个是桂枝汤证根本就没解,也是出汗。
那么这要怎么治呢?用葛根黄芩黄连汤主之。我们方才说了,葛根这个药有治下利的作用,同时你大量用也解表,解表解肌嘛。那么,这个由于里边的热,所以他用滋润清凉的葛根这个药来解表,葛根得大量用,你看他用了半斤,葛根与芩连为伍,黄芩、黄连是苦味的收敛药,有治下利的作用。那么葛根配合黄芩、黄连,一方面去热,一方面治利。黄芩、黄连咱们常用啊,治下利用苦寒药只要是热利就行,像白头翁汤啊,这都是用苦寒。可是苦寒药不全治下利,栀子就不行,黄连、黄芩、黄柏、秦皮、白头翁这类药都有收敛的作用,所以能够治下利。那么大黄更不行了,栀子那也是苦寒的药了,所以苦寒药咱们也得分析。
这个方子,它一方面用葛根,大量用,解肌解表;一方面伍以黄芩、黄连来治协热下利。那么甘草呢,咱们常说它是调百味,其实它在这儿也起作用,它治急迫。你们看看这个证急迫不?下利不止,喘而汗出,都有急迫的症状,这个病现急迫之情,这个时候都用甘草,急迫啊。
所以(葛根芩连汤)这个方剂(适用于)表不解,里有热,下利不止。有里热,是热就易往上,所以反而汗出。那么这个方剂,也很好理解,它以葛根为主药,葛根伍以甘草,它是解肌、解表;伍以黄芩、黄连而治协热下利。
葛根也要先煮,但是不用去沫子。麻黄去沫子是因为麻黄这味药的沫子有点副作用,(麻黄)上面这个沫子,使人头晕,所以用麻黄的时候要去沫子。葛根这个药,溶解于水的时间比较久一点,所以它要先煮。一般这个方剂(葛根芩连汤)在治痢疾的时候,要有表证不可以用葛根汤。这种下利有用葛根芩连加甘草的机会,尤其是小儿痢疾的时候用这个方子的机会挺多。葛根要是用少了,它不起解表作用的。
任应秋《伤寒论语译》
太阳病,桂枝证,医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黄芩黄连汤主之。促,一作纵。
葛根黄芩黄连汤方
葛根半斤甘草二两,炙黄芩三两黄连三两
上四味,以水八升,先煮葛根,减二升,内诸药,煮取二升,去滓,分温再服。
【校勘】《玉函经》《脉经》《千金翼方》:”遂”字在”利”字上;”脉”字上有”其”字。
葛根黄芩黄连汤方。《千金要方》《外台秘要》:方名作”葛根黄连汤”。《外台秘要》:葛根”半斤”作”八两”;”黄芩”下有”切”字。成无己本:葛根作”二两”。《外台秘要》:”黄连”下有”金色者”三字。《玉函经》:”味”字下有”?咀”二字。《外台秘要》:”味”字下有”切”字;”二升”下,有”掠去沫”三字。
【句释】”桂枝证”,即是用桂枝汤的证候,也就是太阳中风证。医反下之,桂枝证是表证,便应用桂枝汤解表,这是治疗的原则,表证不解表而用下剂,便违反了治疗原则,这不合理的疗法,便称作”反”。
【串解】成无己云:”桂枝证者,邪在表也,而反下之,虚其肠胃,为热所乘,遂利不止,邪在表,则见阳脉……促为阳盛,虽下利而脉促,知表未解也。”
要知道体温和血循环是分不开的,太阳病桂枝证,本是肌表充血,血热在表,用发表解肌的方法,便热散而病减,今反用下剂,便引起腹腔里的充血,便由表热一变而为里热的腹泻症。虽如此,脉搏还有促急的现象(参看第21条),是机体的正气仍有趋于体表的机势,这时应该对准证候,适当地选用桂枝汤、葛根汤、桂枝加葛根汤等,仍从表解。假使误下后,脉不促,而有喘息、出汗等情况时,这是热已陷里了,便只有用清里法,而选用葛根黄芩黄连汤,所以成无己说:”喘而汗出者,为因喘而汗出也,即里热气逆所致。”
【语译】患太阳中风证,应服桂枝汤解表,假使不解表而用泻下剂,便会引起严重的腹泻。这时诊察他的脉搏,如有亢奋急促的形象,说明机体抗力仍有从表解的趋势,应及时酌用解表的方剂。假使腹泻而脉搏不促,并有喘息、出汗的情况时,这是已经转变成里热证了,可给以葛根黄芩黄连汤方。
【释方】陆渊雷云:”凡有里热,而病势仍宜外解者,皆葛根芩连汤所主,利与喘汗,皆非必具之证,黄芩、黄连,俱为苦寒药,寒能泄热,所谓热者,充血及炎性机转是也,黄连之效,自心下而上及于头面,黄芩之效,自心下而下及于骨盆,其证候皆为心下痞,按之濡而热,或从种种方面诊知有充血炎性机转者,是也。”
陆氏之说,系根据诸”泻心汤”而言,因为诸泻心汤,都以”心下痞满”为主症,”心下痞满”是内部脏器有充血的病变,所以都属于里热证,都用芩、连。
刘渡舟《伤寒论诠解》
太阳病,桂枝证,医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黄连黄芩汤主之。
葛根黄芩黄连汤方:
葛根半斤 甘草二两,炙 黄芩二两 黄连三两
上四味,以水八升,先煮葛根,减二升,内诸药,煮取二升,去滓,分温再服。
【解析】
本条论述里热夹表邪下利的证治。
病为太阳中风桂枝汤证,医误用下法,而使表邪内陷入里,出现腹泻不止的症状。”医反下之”,是病在表不当下而下,故加一”反”字,此应看做是病机转折的一个条件,临证切不可拘泥。表邪入里以致”利遂不止”,究属虚属实属寒属热,应凭脉辨证以作出诊断。”脉促者”,即脉数而促迫,非为数而中止之促脉。脉数为里有热,且反映人体阳气为盛。阳气盛,有抗邪外达之势,则表邪未能全部内陷,故曰”表未解也”。既有表邪未解,又有里热下利,故可称之为里热夹表邪而下利,或称”协热利”。表邪束肺,里热迫肺,肺气不利故喘。里热逼迫津液外越故汗出。表里皆热,而发热一证也自在言外。既为热利,其大便黏秽,暴注下迫,下利肛热等证则在所不免。治疗采取解表清里,表里两解的方法,用葛根黄芩黄连汤。
葛根黄芩黄连汤是《伤寒论》中以葛根为主药的方剂之一,然葛根用至半斤,则是罕见的。葛根味辛性凉,既可解肌热,又可清肠热,还可升胃肠津气。先煎是取其解肌清肠为主。黄芩、黄连苦寒专清里热,坚阴以止利,加甘草扶中护正,调补下利之虚,助正以祛邪,如此表解里清则利止喘平。从本方用药来看,知此证中表邪少而里热多,可以说仅有三分表证,而七分则是里证。
综上所述,葛根汤既可用于风寒在表,太阳经输不利,项背强几几之证,也可用于太阳、阳明合病,正气抗邪于表而不能顾护于里,里气不和,升降失常,下利呕吐等证。而葛根芩连汤则用于表里皆热、协热下利之证。以葛根为主药的这两个方子,为临床所常用,且疗效也好,应掌握其脉证。
倪海厦《伤寒论》
太阳病,桂枝证,医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黄芩黄连汤主之。
原本有桂枝表证,被医生攻下,或不小心吃坏肚子造成下利,结果利下不止,脉促,喘而汗出者,表末解也,也就是病人被攻下,血都往下跑,血往下力量很强,脉会跳得很快稍微停一下,这时葛根汤没用,要用葛根黄芩黄连汤,有表证,误下,造成表邪,就是表面的病毒渗透
到汗腺里,进入肠子,血往下走,病毒跟着下来,像阿米巴痢疾,可以用葛根黄芩黄连汤。黄芩、黄连是非常寒凉的药,所以它能去热,热就是炎,所以也是消炎的药,黄芩黄连不仅可以内服,还可以外敷,如果皮肤破,可用黄芩黄连。如果化脓,可以加去湿的药,黄芩杀菌的力量很强,阿米巴痢疾的时候,大肠的壁都破洞了,下利都是血,下利久了人会脱水,所以用葛根升水,用炙甘草,把肠子的津液补足,用黄芩、黄连解毒,黄芩、黄连等量,小儿之痢疾炽热难用下剂之证多效。
表邪未陷者,重于解表,已陷而成为里热者,重于清里,本来是桂枝汤证,结果下利,这时候要重于清里,改成葛芩连汤,虚寒者为脉微无力,实热者为脉数有力,为什么摸到脉数?就是里面有东西堵到了,发炎了,病人会发烧。虚寒者舌苔淡白,实热者为舌红苔黄,实热者为舌苔黄的,黄的再进就红,再进就黑了,就是壮热了。虚寒者为下利不热,色黄淡,实热者下利热灼,色黄赤而臭热,肛门没有灼热的感觉,就是不热,实热的大便很臭,而且肛门有灼热的感觉。
葛根黄芩黄连汤方
葛根半斤 甘草二两炙 黄苓三两 黄连三两
右四味,以水八升,先煮葛根,减二升,内诸药,煮取二升,去滓,分温再服。
阿米巴痢疾的时候,大剂的用,葛根可以用到六七钱,如果不大量的用葛根,病人下利不止会脱水,如果没有葛根黄芩黄连汤,寒利可以灸肚脐,热利的时候针曲池、合谷、天枢、关元、三阴交。有临床上的案例西医所谓的肠病毒的案例,其实就是表邪下陷,到了肠子变成热利,所以有葛芩连汤证的时候,结果病人喝到葛芩连汤,病人觉得不苦,反而觉得很甜很好喝。
张胜兵《张胜兵品<伤寒>》
太阳病,桂枝证,医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黄芩黄连汤主之。
葛根黄芩黄连汤方
葛根半斤,炙甘草二两,黄芩三两,黄连三两。
上四味,以水八升,先煮葛根,减二升,纳诸药,煮取二升,去渣,分温再服。
以下解读内容为精简版,详细解读请查看:第30讲 :张胜兵品《伤寒》之太阳病(34条条文·葛根芩连汤)
这一条条文自古以来争议颇多,众说纷纭。以下是我个人的理解,仅供大家参考。
翻译:
太阳病,表现为桂枝汤证,本应采用汗法治疗,但医生却错误地使用了下法,导致患者腹泻不止,脉象急促。这种情况表明表证尚未解除。若患者出现气喘、汗出等内热症状,则应使用葛根黄芩黄连汤治疗。
葛根黄芩黄连汤方:
葛根半斤,炙甘草二两,黄芩三两,黄连三两。将以上四味药用水八升,先煮葛根,煮去二升水分后,加入其他药物,煎成二升,去掉药渣,分两次温服。
成无己在《注解伤寒论》中对此条文的解释较为模糊,他自己似乎也未完全理解。他提到:“不宜下,而便攻之,内虚热入,协热遂利。桂枝证者,邪在表也,而反下之,虚其肠胃,为热所乘,遂利不止。邪在表则见阳脉,邪在里则见阴脉。下利脉微迟,邪在里也。促为阳盛,虽下利而脉促者,知表未解也。病有汗出而喘者,为自汗出而喘也,即邪其外甚所致。喘而汗出者,为因喘而汗出也,即里热气逆所致,与葛根芩连汤,散表邪、除里热。”
成无己的解释并未触及核心问题。关键在于“脉促者,表未解也”。桂枝证本为太阳中风表虚证,脉象浮缓。误用下法后,患者腹泻不止,脉象却变为“促脉”。这里的“促”并非结代脉,而是指脉象急促。
参考第21条条文:“太阳病,下之后,脉促胸满者,桂枝去芍药汤主之。”这里也出现了“脉促”。误下后,邪气内陷于胸,弥漫于胸腔,因芍药具有收敛之性,不利于胸满症状,故用桂枝去芍药汤。这里的“脉促”表明表证未解,正气仍在努力解表。
误下后,表证未解,一部分邪气内陷,一部分邪气仍在表。正气奋起抵抗,气机上冲,导致脉象急促。这说明表证仍然存在,若表证不存在,正气不会外达。因此,“脉促”实际上是误下后,正气上冲解表的表现。
然而,葛根黄芩黄连汤中并无解表寒的药物。若表未解是指表寒未解,则难以解释此方的应用。葛根虽能解表,但单独使用不能治疗太阳中风或伤寒。葛根是辛凉解表药,这里的“表未解”并非指表寒未解,而是指表证已由寒变热,部分表证未解。
打个比方:假设一个人平时胃肠有湿热,某天感染了风寒,出现桂枝汤证。医生误用下法,导致患者腹泻不止,出现喘、汗出、脉象急促等症状。此时,患者已不怕冷、不怕风,但仍有部分表证。腹泻的粪便秽浊黏腻,类似于湿热痢。此时,应使用葛根黄芩黄连汤治疗。
通过这个例子,大家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了。这条条文针对的是那些平时胃肠有湿热的人,得了桂枝汤证后,误用攻下法,风寒入里化热。原本的太阳表证直接转化为阳明里证,形成阳明里热。而阳明里热与体内湿气相夹杂,导致湿热痢的下利不止。
有人会问,你怎么知道有湿气呢?因为如果病人是阳明实火,没有湿气,太阳表证入里化热可能会变成阳明腑实证的承气汤类证,而不是葛根芩连汤证。
还有人会问,病人感受风寒,误下入里后,凭什么说它化热了?风寒靠什么化热?一个寒邪怎么突然变成热邪了?而且还变成表里同热?
我刚才已经解释了,风寒入里化热是因为阳明热盛,而表证未解。此时,阳明的热气上冲而出表,原来的伤寒表证不复存在,而是阳明腑热出经,到了阳明经。此时,不是太阳经,而是阳明经。阳明经热迫津外泄,所以流汗。阳明热上冲出表出经,迫肺导致肺气不降而喘。所以,阳明热盛上奔,迫肺则喘,出表迫津,外泄则汗,阳明表热盛,故脉促(急促)。
通过这种方式解释,假设一个情景模式,情景还原,就可以完全解释通第34条条文。
至于很多医家说这一条是协热下利,哼哼!协热!协哪里的热?感受的是风寒,本来是桂枝汤证,误用攻下法,就协热下利了?即使下利,也是协寒吧!因为桂枝汤本为风寒。协热下利?解释不通啊。
风寒到了阳明变成热,前提是感受风寒的人素体阳明有湿热,即胃肠有湿热。寒邪入里化热是因为阳明胃本来就有热。可以这样理解:吃过火锅吧?把胃和肠想象成一个正在烧开的火锅,点了一份从冰箱拿出来的羊肉,等同于寒邪。寒邪丢到火锅里,火锅变凉还是肉变热?显然是肉变热了。这叫风寒入里化热。
所以,冰冷的羊肉扔到沸腾的火锅里,一定变热。外面的风寒进入本身阳明有湿热体质的人体内,就像羊肉入火锅,当场变热。寒冷的羊肉也变热了。这叫风寒入里化热,随阳明的热变成热邪。再加上误下和体内有湿,如果体内没有湿,可能会变成阳明腑实证(承气汤类)。体内有湿,湿气与热夹杂,导致利遂不止的临床表现。
风寒入里化热,阳明内热很盛,表证未完全解除。风寒入里化热大约七分,还有三分风寒在表,表证未解。阳明阳气上冲,外出解表,太热了,出去后不仅解了表邪,反倒有一部分邪(热)气留在阳明经,变成阳明经热的表热证。
葛根芩连汤表里双解,以解里为主,解表为辅。即使没有表证,葛根黄芩黄连汤也可以用。歌诀里说“无论有表无表”,不管有没有表证,葛根黄芩黄连汤都可以治。因为表证已不明显,变成表热,而非表寒。桂枝汤证已不存在。如果有桂枝汤证,葛根黄芩黄连汤不可能治桂枝汤证。葛根解表,解的是辛凉表,所以解表热。
《伤寒论》好多条文省略了病人的素体体质问题。要通过以方测证,用所学知识推测可能的情况。即情景再现。为什么会有这条条文?张仲景通过哪种情景写出来、总结出来的?这种思维方式对学习《伤寒论》非常重要。
在这里,我必须举几个葛根芩连汤的病案,精彩绝伦。
曾治过一例克罗恩病病人。克罗恩病在西医认为是自身免疫性疾病,无法根治。临床表现是拉肚子。接诊的病人一天拉30多次,只能守在厕所旁,过一会儿就要拉,没有实质性治疗方法。通过辨证发现病人本身是湿热体质,选用葛根芩连汤。
但事情没那么简单。病人病得久,合并复发性口腔溃疡。克罗恩病在西医上没有好方法,时间推移,常伴有肠道溃疡、口腔溃疡等。用葛根芩连汤合甘草泻心汤,治疗每天30多次拉肚子和复发性口腔溃疡,加减化裁调治几个月,病人恢复正常,大便控制在两三次,口腔溃疡也解决了。
这个病印象很深刻。病人说准备自杀,因为受不了,嘴巴总烂,大便一天30几次,无法正常生活。说如果在这里治不好,就准备自杀,遗书都写好了。压力山大,治不好岂不是间接杀人?还好,用了张仲景《伤寒论》里的两个方子:葛根黄芩黄连汤和甘草泻心汤。
耐心指导病人不要吃辛辣,饮食清淡。因为体内有湿热,是素有阳明湿热体质的人。得克罗恩病,西医说是自身免疫性疾病,在我看来,可能是曾几何时得了一场感冒,误用下法或其他原因,风寒入里化热。病邪怎么来,就让它怎么走,可能是风寒入里化热,积于阳明肠,按治疗清阳明肠热的方式解决。有口腔溃疡,用甘草泻心汤,和解中焦气机,因为甘草泻心汤是和解剂,和解寒热,寒热交错出现气机不利的口腔溃疡或白塞氏病。《伤寒论》治好了,跟我没关系。
再举一例肠癌。接诊一例肠癌病人,一天拉二三十次,每次拉的不多,和克罗恩病不一样。也是湿热下注,胃肠有热,选用葛根芩连汤。为加强疗效,在葛根芩连汤基础上加马齿苋。因为肠癌,读过《攻癌救命录》知道,肠癌常用红藤和败酱草联合用药。
所以在葛根芩连汤基础上加马齿苋、红藤、败酱草。病人肚子还疼,加芍药。每次不多,次数多,加行气药,行气导滞,用木香、槟榔、厚朴、枳实。反复加减,湿热一除,用木香、槟榔、枳实、厚朴把垃圾一次性往外推。治疗一段时间后,大便变成两三次,基本恢复正常。
肠癌在癌症里治愈率比较高。特别是溃疡性肠癌。如果有实质性瘤体的肠癌,产生肠梗阻,不能这么治。实质性瘤体导致肠梗阻,和溃疡性肠癌治法完全不同,叫同病异治。
今天这两个病案:克罗恩病和溃疡性肠癌,都属于阳明湿热,都能用葛根黄芩黄连汤治疗。
张仲景在《伤寒论》里没告诉我们葛根芩连汤能治克罗恩病、溃疡性肠癌,但我们用葛根芩连汤治这些病。为什么呢?因为张仲景只告诉理法方药,理法方药里埋着玄机,得自己悟。只有自己悟出来的东西,才是真正掌握的东西。听我讲课,我只是把自己悟的东西讲给大家听,不是把所学的东西强行塞给大家,而是希望通过悟道、悟医的过程给大家启发,让大家自己能悟道、悟医。因为“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最后编辑于 04-24 · 浏览 17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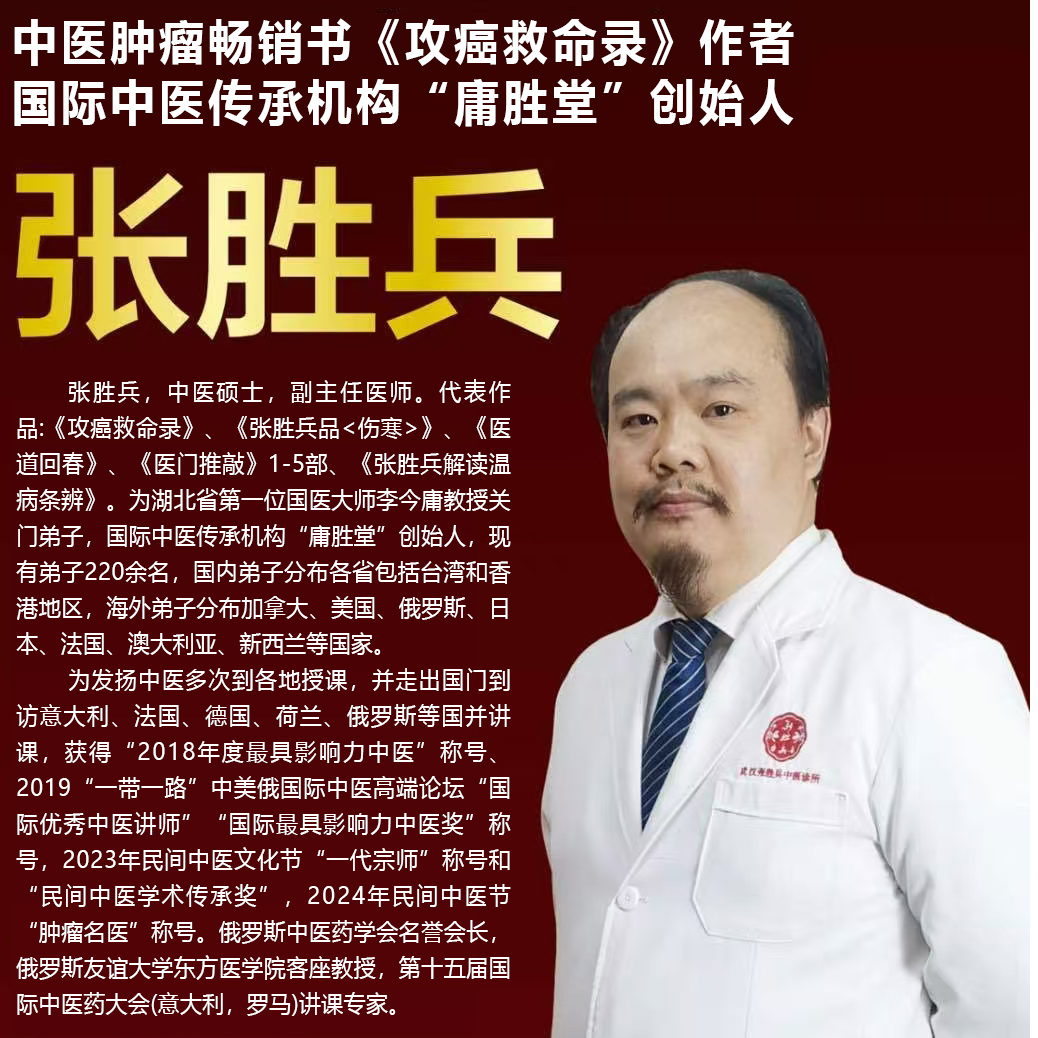
 伤寒论名家解读汇编
伤寒论名家解读汇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