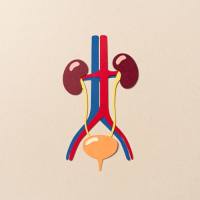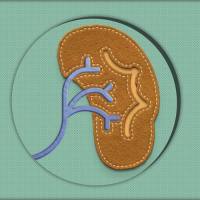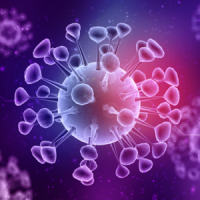围产期抑郁筛查与干预移动平台的应用与效果评价研究
围产期抑郁是指妇女在妊娠期间及分娩后1年内出现的抑郁障碍,根据发生时段可分为产前抑郁和产后抑郁[1]。围产期抑郁通常表现为孕产妇持续性的情绪低落、兴趣丧失、睡眠和/或进食障碍等症状,严重时可能导致自杀倾向。而对子代而言,围产期抑郁可能增加早产风险,影响婴幼儿的发育,并对其认知、社交和情感发展产生长期的不利影响。此外,孕产妇的抑郁症状还可能破坏亲密关系,引发家庭矛盾甚至家庭结构破碎,同时加重公共卫生和社会保障系统的负担[2-5]。根据NISAR等[6]Meta分析结果,我国大陆地区围产期抑郁的合并患病率为16.3%,其中产前抑郁为19.7%,产后抑郁为14.8%,这些比率处于中低收入国家水平(19%~25%)和高收入国家水平(7%~15%)之间。鉴于围产期抑郁作为影响妇女儿童健康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对其有效管理迫在眉睫。
普遍筛查、尽早干预已被证实是能有效改善围产期抑郁的措施[7-8]。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用“互联网+心理干预”模式已成为围产期抑郁管理的趋势。国内外已有多项研究证明了该模式的有效性[9-12]。然而,现有研究大多样本量较小,且主要关注孕晚期和产后阶段,尚缺乏大样本量下覆盖孕产期全程的研究证据。深圳市自2013年起由地方财政出资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产后抑郁筛查与干预工作[13],2019年进一步启动围产期抑郁筛查与干预项目[14]。该项目由产科医务人员和社区产后访视人员在常规孕检和产后访视流程中对所有孕产妇开展抑郁筛查,并对筛查结果呈阳性的妇女进行分级转诊和随访管理。自2021年起,该项目依托“深圳妇儿通”小程序,结合深圳市妇幼保健管理信息系统,通过移动平台建设进一步推进项目实施。建成的平台为孕产妇提供覆盖生育全程的心理健康服务,从孕早期直至产后6周,打造了“互联网+孕产妇心理健康服务”的新形态、新模式。
本研究利用深圳市妇幼保健管理信息系统中的项目常规数据,通过回顾性比较接受常规服务的孕产妇和使用移动平台服务的孕产妇的抑郁筛查率、筛查阳性率、转诊率以及干预率等指标的差异,分析移动平台对促进围产期抑郁筛查与干预项目实施的效果,探究目前最显著的实施瓶颈,以期为促进该平台的优化完善及应用推广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1)2020年6月—2022年5月在深圳市任一助产医疗机构(全市10个辖区共82家)分娩的孕产妇;(2)围产期抑郁筛查与干预个案记录在深圳市妇幼保健管理信息系统中可查;(3)自愿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1)患有严重精神类疾病或智力障碍的孕产妇;(2)合并某些躯体疾病导致问卷填写困难或不能有效沟通。研究人员将符合纳入标准的所有孕产妇个案记录从深圳市妇幼保健管理信息系统后台导出,建立基础数据库。所有参与者在首次筛查时已充分了解研究内容并同意参加,所收集到的孕产妇资料严格保密,仅限研究团队成员使用。本研究通过深圳市妇幼保健院科研伦理委员会审批(批件号:SFYLS[2021]066)。
1.2 围产期抑郁筛查量表
1.2.1 患者健康问卷(Primary Health Questionnaire,PHQ-9):PHQ-9包括9个条目,是根据美国精神病学会1994年出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DSM-Ⅳ)中的抑郁症状学标准编制的抑郁自评量表。该问卷信效度较好,常用于临床实践中抑郁症状的筛查和严重程度评估[15]。每个问题的回答由“完全不”到“几乎每天”按0~3分评分,总分0~27分,得分越高表示抑郁症状越严重。本研究参照国内外文献[16-17],以研究对象在孕早期、孕中期和孕晚期的PHQ-9评分≥5分为产前抑郁筛查阳性,作为孕期转诊和干预的标准。
1.2.2 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d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EPDS):EPDS包括10个条目,1998年由LEE等[18]翻译成中文版,之后在我国被广泛应用于产后抑郁的筛查及相关研究,显示出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该量表每个条目的描述按0~3分评分,总分0~30分,得分越高说明抑郁症状越严重。本研究参照国内外文献[19-20],以研究对象在产后2~6周的EPDS得分≥10分为产后抑郁筛查阳性,作为产后转诊和干预的标准。
1.3 研究分组
依据移动平台的正式启用时间,研究人员将参与者分为两个组别:常规服务组(2020年6月—2021年5月分娩)和移动平台组(2021年6月—2022年5月分娩)。两组分别接受的围产期抑郁筛查与干预服务如下。
1.3.1 常规服务组:根据《深圳市围产期抑郁筛查与干预项目方案》[14],产科医务人员在常规孕检时指导孕妇填写纸质版PHQ-9,在孕早期(孕13周前)、孕中期(孕16~24周)、孕晚期(孕25~32周)分别筛查至少1次,具体筛查时间根据孕妇的就诊时间而定;社区产后访视人员在上门访视时(产后2~6周)指导产妇填写纸质版EPDS。产科医务人员或产后访视人员为筛查结果呈阳性的孕产妇现场发放围产期抑郁防治宣教资料,并提醒其前往所属辖区妇幼保健机构心理门诊进行确诊或心理干预;将存在重度抑郁障碍的孕产妇转诊至精神专科医院或综合医院精神科进行治疗。产科医务人员或产后访视人员通过电话对筛查阳性孕产妇进行至少4周的追踪随访,收集其是否就诊、就诊机构、接受何种心理干预/治疗以及抑郁症状变化等信息。所收集的孕产妇资料均人工输入深圳市妇幼保健管理信息系统。
1.3.2 移动平台组:深圳市围产期抑郁筛查与干预移动平台包含多个模块,其中用户模块为孕产妇提供一系列移动端服务,包括孕产保健信息查询、心理健康评估、母婴健康知识学习、孕妇学校预约等;医务人员模块可实现孕产妇抑郁筛查结果查询、阳性筛查结果提醒、“一键”转诊等功能;管理人员模块功能则包括个案追踪管理、健康知识宣教、数据质量控制等功能。基于该平台,产科医务人员在常规孕检时指导孕妇从移动端在线填写PHQ-9,在孕早期、孕中期、孕晚期分别筛查至少1次,具体筛查时间根据孕妇的就诊时间而定;社区产后访视人员在上门访视时指导产妇从移动端在线填写EPDS。产科医务人员或产后访视人员通过平台实时查询孕产妇抑郁筛查结果(平台自动识别阳性结果),提醒筛查阳性孕产妇在移动端挂号就诊,或将其直接“一键”转诊至所属辖区妇幼保健机构心理门诊或精神专科医院/精神科,并对其进行至少4周的追踪管理。市、区两级项目管理人员通过平台查询已转诊的孕产妇信息,主动对未及时就诊的孕产妇进行电话随访。所收集的孕产妇数据大部分可自动同步到深圳市妇幼保健管理信息系统。此外,项目管理人员通过平台为所有注册使用“深圳妇儿通”的孕产妇定期推送围产期抑郁防治宣教资料,形式包括公众号推文、短视频等。
1.4 质量控制
深圳市妇幼保健院作为围产期抑郁筛查与干预项目的实施牵头单位,定期利用深圳市妇幼保健管理信息系统开展全市项目数据的质量控制,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各辖区妇幼保健机构也定期对辖区内数据进行质量检查,以维护数据的准确性和及时性。此外,每个助产医疗机构在产科或预防保健科都安排专人负责监督项目实施,以确保项目有效运行。在本研究中,研究人员共获取317 634条孕产妇个案记录,为确保数据质量,对基础数据库进行反复检查,识别并删除重复数据、排除违反已知逻辑的数据,并对数据格式进行标准化处理,最终保留311 719条(98.1%)有效数据。
1.5 统计学方法
研究人员将有效数据库导入SPSS 26.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观察指标包括孕早期、孕中期、孕晚期以及产后的抑郁筛查率、筛查阳性率、转诊率以及干预率。筛查率计算公式为:有筛查结果的人数/总人数×100%;筛查阳性率计算公式为:筛查阳性人数/筛查人数×100%;转诊率计算公式为:有转诊记录(已收到转诊提醒或已由平台“一键”转诊)的人数/筛查阳性人数×100%;干预率计算公式为:有干预记录(随访数据显示已到相应医疗机构就诊)的人数/筛查阳性人数×100%。计量资料以(x±s)表示,计数资料以例数(%)表示。计数资料的分析采用χ2检验或趋势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由于本研究使用的是公共卫生项目的常规数据,部分条目存在数据缺失。考虑到缺失数据的比例较小,且本研究未进行孕产妇一般情况与各观察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分析,认为这不会对主要结论产生显著影响,因此未对数据进行删除或插补处理。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本研究共纳入311 719名孕产妇,平均年龄(29.7±4.5)岁。根据移动平台启用时间对孕产妇进行分组,常规服务组166 832人,移动平台组144 887人。两组孕产妇年龄均集中在25~35岁,占比均在70%以上;职业主要为干部/公司职员,占比均超过50%;教育水平以大学/大专为主,占比均超过55%;报告有精神病史或家族病史的占比均低于0.3%。两组孕产妇年龄、职业、教育水平以及家族病史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 两组孕产妇围产期抑郁筛查情况
与常规服务组相比,移动平台组孕早期、孕中期、孕晚期以及产后抑郁筛查率均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2.3 两组孕产妇围产期抑郁筛查阳性情况
移动平台组孕早期、孕中期抑郁筛查阳性率均高于常规服务组,孕晚期、产后抑郁筛查阳性率均低于常规服务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2.4 两组孕产妇围产期抑郁转诊情况
与常规服务组相比,移动平台组孕早期、孕中期、孕晚期以及产后抑郁转诊率均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2.5 两组孕产妇围产期抑郁干预情况
与常规服务组相比,移动平台组孕早期、孕中期、孕晚期以及产后抑郁干预率均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2.6 移动平台启用后围产期抑郁筛查率和阳性率趋势分析
图1展示了移动平台启用后1年内孕产期各阶段的抑郁筛查率和阳性率趋势。孕早期(χ2趋势=13 902.862,P<0.001)、孕中期(χ2趋势=5 577.567,P<0.001)、孕晚期(χ2趋势=4 886.518,P<0.001)抑郁筛查率均持续提升,尤其是孕早期从41.0%上升至80.4%。产后筛查率在平台启用初期已达到94.5%,之后进一步提升至97.1%(χ2趋势=270.489,P<0.001)。孕早期筛查阳性率呈上升趋势(χ2趋势=178.878,P<0.001),由平台启用初期的10.6%上升至15.5%。孕中期阳性率在6%~8%轻微波动(χ2趋势=24.583,P<0.001)。而孕晚期阳性率(χ2趋势=30.218,P<0.001)和产后阳性率(χ2趋势=65.369,P<0.001)则呈逐步下降趋势,分别从8.3%和3.1%下降至7.2%和2.2%。

2.7 移动平台启用后抑郁筛查阳性孕产妇转诊率和干预率趋势分析
图2展示了移动平台启用后1年内抑郁筛查阳性孕产妇的转诊率和干预率趋势。综合全年数据来看,孕产期各阶段的转诊率总体维持在较高水平,除孕早期呈上升趋势(χ2趋势=110.218,P<0.001)外,其余基本在95%以上。然而,抑郁筛查阳性孕产妇的干预率却整体偏低。尽管平台启用后孕中期干预率(χ2趋势=65.395,P<0.001)、孕晚期干预率(χ2趋势=4.349,P<0.05)均提升,但均未超过20%。与孕期相比,产后干预率上升幅度较为显著(χ2趋势=90.700,P<0.001),从平台启用初期的33.5%持续上升至59.3%。

3 讨论
3.1 围产期抑郁筛查与干预移动平台的有效性
本研究结果显示,深圳市2021年启用的围产期抑郁筛查与干预移动平台对提升孕产期各阶段的抑郁筛查率、转诊率以及干预率均产生了显著影响,并且这些影响在平台启用后持续存在。较之现有研究中大多具有商业性质的围产期抑郁干预平台[9-12],该平台由地方政府主导建设,服务于重点公共卫生项目的实施,具有公益性、可及性强、可接受度高等特点。同时,平台紧密结合项目实施需求,设有用户模块、医务人员模块和管理人员模块,在体现“以患者为中心”的同时具备较强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本研究观察到的筛查率、转诊率和干预率提升可归因于移动平台的多重优势,包括其便利性、易获取性及安全性等特点。与传统的心理干预措施相比,移动健康干预具有功能广泛、节约时间和费用、不受地域限制、交互能力强、保护隐私安全、接受度高等优点[21],同时已被证明能有效缓解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对孕产妇群体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22]。
杨中婷等[4]2023年发表的Meta分析显示,我国妇女孕早期抑郁检出率为24.5%,之后随生育进程呈下降趋势,孕中期、孕晚期以及产后6周的抑郁检出率分别为20.6%、17.8%和17.0%。相比之下,本研究中孕产期各阶段的抑郁筛查阳性率均较低,但总体趋势基本一致。这可能是因为本研究使用了深圳市围产期抑郁筛查与干预项目常规数据,涵盖了更广泛的孕产妇群体,能够更全面地反映真实的抑郁筛查情况,减少了小规模研究中的偏差和不确定性[23]。
此外,本研究观察到平台启用后孕早期和孕中期抑郁筛查阳性率的上升趋势。这与现有研究相符[24-25],可能是因为移动平台具有更高的参与度和便利性,尤其是在疫情期间面对面医疗服务减少的情况下,导致更多潜在病例的发现。同时,移动平台组的孕晚期至产后阶段抑郁筛查阳性率显著低于常规服务组,这反映对围产期抑郁进行早期识别与干预的效果,从而进一步验证了通过移动平台交付心理干预措施的有效性。这一发现与国内外多项研究结果一致[26-27],强调了利用移动技术在公共卫生领域中,尤其是在围产期抑郁防治方面的重要价值和潜力。
3.2 围产期抑郁筛查与干预项目的实施瓶颈
虽然移动平台启用后围产期抑郁的筛查率有显著提升,且超过90%的筛查阳性孕产妇被转诊到市/区级妇幼保健机构心理门诊或精神专科医院/精神科就诊,但是实际接受过心理干预/治疗的比例却普遍偏低,距离项目方案提出的80%目标尚有一定距离[14]。这一现象在孕期尤为严重。THOMBS等[28]系统综述指出,心理干预率过低会使围产期抑郁筛查的效用大幅下降,从而影响整体防治效果。导致筛查阳性孕产妇干预率低的原因是多重的,一方面,心理健康服务可及性差是主要障碍[29],部分妇女会因为担心治疗费用高、交通不便或被污名化而放弃就诊[30]。另一方面,大部分筛查阳性孕产妇只有暂时或轻度抑郁症状,仅需简单的心理健康支持,无需前往专业机构就诊[31]。在湖南省一项队列研究中,80%不接受心理咨询的孕产妇认为“自己可以处理抑郁症状”[32]。此外,尽管移动健康干预相对于传统干预措施在提高覆盖率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但也存在一些潜在问题,如信息呈现方式单一、内容缺乏吸引力等,导致用户难以持续使用。因此,未来研究应深入探讨用户的使用偏好以及影响移动平台实施的因素,综合考虑供需双方的立场,为优化平台设计、制订有效且可持续的实施策略提供依据[33]。
3.3 局限性
本研究依赖的数据来源于深圳市妇幼保健管理信息系统,虽然样本量较大,但其结果具有一定的地域性。这意味着研究发现主要反映了深圳市的情况,可能不完全适用于其他地区,从而限制了研究结果的普适性。同时,回顾性数据分析仅能反映移动平台对项目实施的影响,无法评价具体干预措施(如某项心理干预、健康宣教)对减轻孕产妇抑郁症状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常规服务组和移动平台组的年龄、职业、教育水平以及家族病史存在统计学差异。虽然这些差异可能是由于大样本量使得细微的差异变得显著[34],但仍会对研究结果产生一定的混杂效应。同时,由于部分条目存在数据缺失,且本研究未对这些缺失数据进行删除或插补处理,这可能对组间比较的解释力造成一定影响。此外,本研究的开展时间处于疫情期间,当时的社会、经济和医疗环境变化可能对孕产妇的求医行为造成影响。这为理解孕产妇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的心理需求提供了独特的视角,然而特殊时期的环境也可能使得研究结果不完全适用于常态情况[35]。未来研究应在常态情况下对不同的地区进行探索,通过随机对照试验等试验性方法控制混杂因素,评价不同干预措施或干预措施组合对减轻孕产妇抑郁症状的效果,同时探索有效的实施策略,为构建和优化围产期抑郁防治策略提供具有普适性的科学证据。
4 小结
深圳市围产期抑郁筛查与干预移动平台的实施显著提高了围产期抑郁的筛查率、转诊率以及干预率,为围产期抑郁的常态化管理提供了有效的工具和方法。然而,筛查阳性孕产妇干预率偏低是目前最突出的实施瓶颈。未来研究应致力于全面了解孕产妇、医务人员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的需求,不断优化移动平台功能设计,探究最优干预措施组合,增强健康宣教,通过创新方法制订有效的实施策略,从而为探索具有可行性、可持续性和普适性的围产期抑郁防治特色服务模式提供借鉴,促进孕产妇心理健康和福祉。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