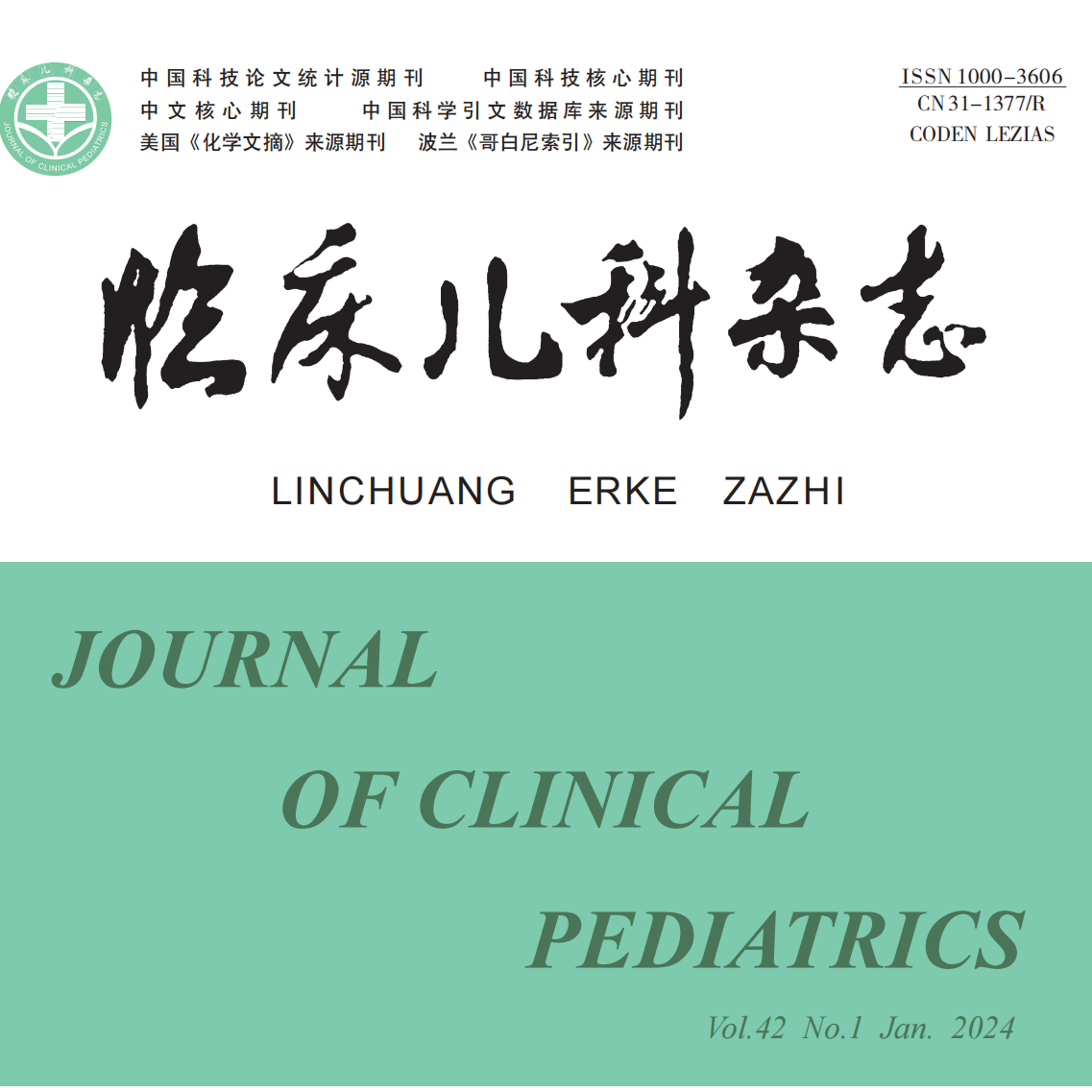2019—2023 年急性呼吸道感染儿童肺炎支原体流行病学特征分析 :一项单中心回顾性研究
本文作者:李铭一 沈袁恒 陈 峰 李媛睿 张敏华 王娟娟 沈立松 蒋黎敏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检验科(上海 200092)
本文推荐引用格式:
李铭一, 沈袁恒, 陈峰, 李媛睿, 张敏华, 王娟娟, 沈立松, 蒋黎敏. 2019—2023年急性呼吸道感染儿童肺炎支原体流行病学特征分析:一项单中心回顾性研究[J]. 临床儿科杂志, 2024, 42(6): 485-490 DOI:10. 12372/jcp.2024.24e0242
LI Mingyi, SHEN Yuanheng, CHEN Feng, LI Yuanrui, ZHANG Minhua, WANG Juanjuan, SHEN Lisong, JIANG Limin.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Mycoplasma pneumoniae in children with acute respiratory infections from 2019 to 2023: a single-center retrospective study[J]. Journal of Clinical Pediatrics, 2024, 42(6): 485-490 DOI:10.12372/jcp.2024.24e0242
摘要:目的 探讨上海单中心COVID-19大流行前、中、后期急性呼吸道感染(ARTI)患儿肺炎支原体(MP)及其他病原体阳性率的变化。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0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行呼吸道五联检和流感病毒三联检的ARTI患儿的临床资料。结果 共纳入ARTI患儿91825例次,男48729例次、女43096例次,中位年龄为5.0(3.0~8.0)岁。疫情前组14096例次,呼吸道病原体阳性5126例次(36.4%);疫情中组13366例次,阳性2963例次(22.2%);疫情后组64363例次,阳性33510例次(52.1%)。疫情前、中、后组ARTI患儿之间男性比例、年龄分布、各病原体阳性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疫情前和疫情后组>6岁患儿比例较高,而疫情中组0~3岁比例较高(P<0.014)。2019—2023年不同年份以及不同月份之间MP阳性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2019年1、2、12月的MP阳性率较高(20.3%~37.7%),2020年1~3月阳性率较高(21.5%~35.3%),2021年仅12月阳性率(25.8%)高于20.0%,2022年1年的阳性率均低于20.0%,2023年4~6月、8~12月的阳性率均较高(21.5%~37.2%)。MP阳性患儿23247例次,疫情前、中、后组之间性别、年龄分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疫情前和疫情后组MP阳性患儿中>6岁比例较高,疫情中组0~3岁比例较高(P<0.014)。结论 在2019—2023年期间,以MP为代表的各种ARTI相关病原体的流行病学特征发生了一定变化,MP的好发年龄分布和季节流行病学特征发生了显著改变。
关键词:COVID-19;急性呼吸道感染;肺炎支原体
2023年以来,儿童急性呼吸道感染(ARTI)率居高不下,对各大医院儿科诊疗系统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在此次呼吸道感染潮中,各种ARTI相关病原体的流行高峰期不断涌现,尤其以肺炎支原体(MP)为主。有专家认为,2023年7月开始的 MP流行高峰出现了新的特征,而此次MP的另一个流行病学特征为大环内酯类耐药病例占比高,且容易发展成重症[1]。国内有研究者发现5岁以下儿童的呼吸道合胞病毒(RSV)IgG抗体水平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大流行期间显著下降,尤其年龄较大的儿童,推测此次流行病学的转变可能与大流行期间有关的防护措施,例如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居家学习和工作等所造成的免疫债务有关[2-3]。另有国内研究分析了2023年4月至10月呼吸科住院患儿MP感染的流行病学特征和耐药率,推测本次流行中MP可能存在新的突变[4]。
鉴于此,本研究分析了2019—2023年上海地区单中心ARTI患儿相关病原体的阳性率,旨在了解各病原体尤其是MP在COVID-19疫情前、中、后期的流行病学特征,为研究儿童呼吸道感染病原体提供证据,并为ARTI的诊治和防控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0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门急诊就诊以及住院并接受了呼吸道病原体检测的所有ARTI患儿的临床资料。纳入标准:①年龄范围0~14岁;②符合ARTI诊断标准[5];③标本类型为全血;④完成ARTI相关病原体检测项目,包括呼吸道五联检,即MP IgM抗体、肺炎衣原体(CP) IgM抗体、RSV IgM抗体、腺病毒(ADV) IgM抗体、柯萨奇B组病毒(Cox-B)IgM抗体,以及流感病毒三联检,即流感病毒A型(Flu-A)IgM抗体、流感病毒B型(Flu-B)IgM抗体和副流感病毒(PIV)IgM抗体。排除标准:临床资料不完整。
本研究获得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No.XHEC-D-2024-052 )。
1.2 方法
1.2.1 临床资料收集 通过医院信息系统(HIS)收集患儿门诊号或住院号、性别、年龄、就诊科室、临床诊断、采样时间和相关病原体检测结果。
1.2.2 样本采集与ARTI相关病原体检测方法 在门急诊或入院72小时内由专业人员按照常规方法采集全血样本(末梢血100μL或静脉血2~3mL)。呼吸道五联检采用MP IgM抗体、CP IgM抗体、RSV IgM抗体、ADV IgM抗体、Cox-B IgM抗体联合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医疗器械注册编号 :国械注准20163401650);流感病毒三联检采用Flu-A IgM抗体、Flu-B IgM抗体和PIV IgM抗体联合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医疗器械注册编号 :国械注准20163401649)。两种试剂盒均来自北京英诺特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采用免疫捕获法原理检测IgM抗体,分别用鼠抗人IgM(抗μ链)单克隆抗体和羊抗鼠IgG抗体包被的硝酸纤维素膜;胶体金分别标记MP、CP、RSV、ADV、Cox-B、Flu-A、Flu-B、PIV重组抗原和鼠IgG抗体为示踪物包被玻璃纤维素膜载金垫。使用时将5μL待检全血和90μL稀释液加入到样本孔中,如样本血中含有目标IgM抗体时,则分别与胶体金标记的抗原结合成复合物,该复合物在包被的鼠抗人IgM抗体处被捕获,与鼠抗人IgM抗体结合呈现紫红色条带,作为检测线(T)。胶体金标记的鼠IgM抗体与羊抗鼠IgM抗体结合呈现紫红色条带,作为质控线(C)。
1.2.3 结果判读 在样品孔内加入待测样品后15~25分钟内判定结果,25分钟以后显示的结果则为无效。阳性为对应判读窗口T和C位置出现清晰紫红色条带。阴性为对应判读窗口仅在C位置出现清晰紫红色条带。无效为判读窗口C位置无紫红色条带,不论T位置是否出现条带均为无效结果,需要重新检测。
1.2.4 分组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告[6-7],2019年1月1日—2020年1月20日为COVID-19疫情前(疫情前组),2020年1月21日—2023年1月7日为COVID-19疫情中(疫情中组),2023年1月8日—2023年12月30日为COVID-19疫情后(疫情后组)。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23.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以例数(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进一步两两比较采用χ2分割。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疫情前、中、后期ARTI患儿性别、年龄分布及其病原体阳性检出率
共纳入91825例次ARTI患儿,男48729例次、女43096例次,中位年龄为5.0(3.0~8.0)岁。疫情前组14096例次,呼吸道病原体阳性5126例次(36.4%);疫情中组13366例次,阳性2963例次(22.2%);疫情后组64363例次,阳性33510例(52.1%)。
疫情前组、疫情中组和疫情后组 ARTI 患儿之间男性比例、年龄分布、各病原体阳性率、单种以及混合病原体阳性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经卡方分割两两比较发现,疫情前和疫情后组>6岁患儿比例较高,而疫情中组0~3岁患儿比例较高(均P<0.014);疫情后组MP、Flu-A、Flu-B的阳性率较高,单种以及混合病原体阳性率均较高。见表1。

2.2 2019—2023年不同月份MP阳性率分布差异
2019—2023年不同年份以及不同月份之间MP阳性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2019年1、2、12月的MP阳性率较高(20.3%~37.7%),2020年1~3月MP阳性率较高(21.5%~35.3%),2021年仅12月阳性率(25.8%)高于20.0%,2022年全年各月份的阳性率均低于20.0%,2023年4~6月、8~12月的阳性率均较高(21.5%~37.2%)。见表2、图1。


2.3 MP阳性患儿在疫情不同时期性别、年龄分布
MP阳性患儿23247例次,其中男11309例次、女11938例次。疫情前、疫情中和疫情后组之间性别、年龄分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经卡方分割两两比较发现,疫情前和疫情后组 MP阳性患儿中>6岁比例较高,疫情中组MP阳性患儿中0~3岁比例较高(均P<0.014)。见表3。

2.4 疫情不同时期ARTI患儿MP合并其他病原体阳性构成比分析
MP合并其他1种病原体阳性,疫情前组674例次,疫情中组231例次,疫情后组6631例次。疫情前、疫情中和疫情后组之间MP合并其他1种病原体阳性率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48.2,P<0.001),疫情后组MP合并Flu-A比例较高。见表4。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提示,疫情后各种ARTI相关病原体阳性率均有一定程度升高,以MP、Flu-A、Flu-B为主,且无论单种还是混合病原体的阳性率在疫情后均有了明显提高。ARTI与MP阳性患儿的年龄分布也由于疫情出现了变化,疫情前和疫情后组>6岁患儿比例较高,而疫情中组0~3岁比例较高,提示疫情中期无论ARTI还是MP阳性患儿都出现了低龄化的趋势。考虑原因如下:①可能是因为在疫情防护期间低年龄儿童的防疫依从性较弱,无法长时间佩戴口罩和保持手口卫生 ;②在疫情防护期间出生的婴幼儿,其免疫系统可能没有通过早期接触这些病原体来建立足够的免疫记忆[5];③低龄儿童疫苗接种情况不如高年龄儿童完善。
2023年上海MP的流行病学特征也出现了异于往年的改变,流行高峰期频繁出现,阳性率居高不下。2019和2020年MP的流行季节以冬季为主,2021年仅12月出现流行高峰,2022年由于疫情防控并未有MP流行高峰出现,而2023年4月(MP阳性率31.2%)起即出现流行高峰,仅7月有所回落(16.3%),8~12月的阳性率又呈现逐渐上升趋势(23.9%~37.2%),这与Bolluyt等的报道相似[8]。社会对2023年ARTI尤其是MP感染“暴发”的认知,很可能源于这一季节流行趋势的变化。2023年MP流行特征变化原因尚不明确,可能与病原体本身以及宿主有关。据推测MP的流行周期变化是由优势菌株的变化引起的[9]。2023年MP的流行高峰可能符合正常的周期变化,只是由于优势菌株的位移周期较长所致。同时,疫情后群体免疫力下降,可能导致MP易感性升高,而本次流行的MP可能存在致病力更强的新的突变株[4]。此外,COVID-19大流行之后,人们对呼吸道感染性疾病更加重视,2023年各种呼吸道病原体的检测量都呈现大幅度升高,这也是导致MP检出率升高的原因之一。
疫情后期MP合并Flu-A比例升高明显,从疫情前期的21.8%,疫情中期的25.1%,升至疫情后的40.0%;然而MP合并Flu-B比例在疫情前、中、后的变化幅度较小(40.7%~48.0%)。这可能是因为在上海市地区疫情后MP、Flu-A和Flu-B三种疾病在2023年流行病学特征上存在区别。根据中国国家流感中心的流感监测周报可以发现,既往我国南方春季Flu-A流行一般在1月达到高峰并持续到3月份左右,而2023年1月至2月上旬并无明显Flu-A暴发,从2月中旬后Flu-A开始流行并在3月中旬到达上半年阳性率的最高点,而Flu-B仅在2023年11月份出现一个高峰。同时,从本研究结果可以看出,MP的阳性率在2023年的4月和5月出现明显升高。由于2023年Flu-A的流行出现“滞后性”,使得MP与Flu-A在时空上存在更多的交集,延长了两种病原体在儿童人群中的逗留时间,增加了两种疾病的易感性,这可能导致疫情后MP与Flu-A合并阳性例数增多。
关于疫情后各种ARTI相关病原体阳性率升高的现象也见于其他国家,为探究其原因,各国学者相继提出了一些假设,目前大部分讨论集中于“免疫债务”和“免疫盗窃”[10]。“免疫债务”最早由Cohen等[11]法国儿科传染病专家于2021年提出,相应的防护措施减少了人群与各种ARTI病原体的接触机会,使得机体缺乏相应的免疫刺激,同时在防护期间出现儿童计划疫苗接种的延迟和疫苗接种率下降的情况;当疫情得到控制和防护措施解除时,这种“债务”可能会对人体产生负面影响。而另外一些学者更倾向于“免疫偷窃”的假说,他们认为SARS-CoV-2病毒以多种机制损伤人体的免疫力,这可能是其流行结束后各种呼吸道传染病发生率上升的主要原因[12-14]。但具体原因为何,还需更多研究加以验证。
本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分析,所得结论可能存在局限性,需要更多样本量和更长时间跨度的多中心前瞻性研究进一步验证。同时,IgM抗体阳性仅表示当前或最近的感染,并不能确定感染是否正在进行或已经过去。虽然通过胶体金法进行抗体检测可快速获得检测结果,对MP及其他病原体暴发流行期间医疗机构的就医压力有一定缓解作用,但MP及其他病原体感染的诊断应经过临床症状、体征、病史以及实验室检测等多方面综合判断。此外,IgM抗体检测方法也存在一定局限性,为更准确地诊断MP及其他病原体感染,还需结合其他检测方法,如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检测等。
综上,COVID-19疫情后各种ARTI相关病原体阳性率均有一定程度升高,以MP、Flu-A、Flu-B为主,疫情后MP流行病学特征也出现新的变化,可能与相关防护措施影响人群免疫系统功能或MP菌株流行周期变化有关。COVID-19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X疾病”[15],新的流行病暴发只是时间问题。COVID-19疫情后我国不断提升公共卫生应急能力,包括建立未知病原的检测技术,形成更敏感有效的监测预警网络,储备充足的个人防护装备。其次,提升医务人员的临床救治水平和服务能力,以应对突发的医疗需求激增的情况;最后,提升新疫苗的研发技术和生产能力,能够在“X疾病”暴发后在人群中快速建立免疫屏障。
参考文献:略。
最后编辑于 2024-06-21 · 浏览 3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