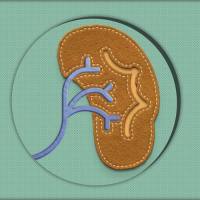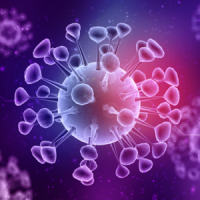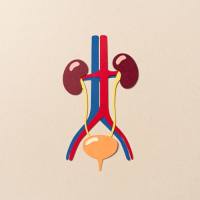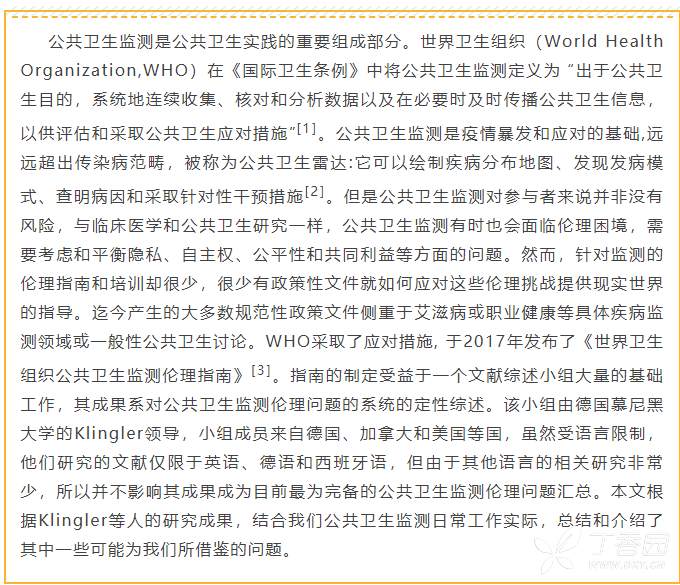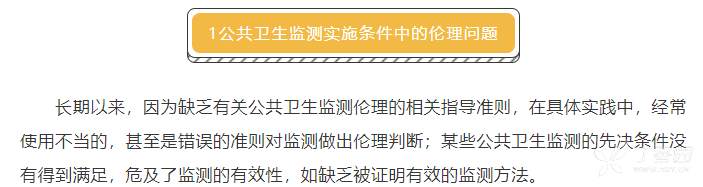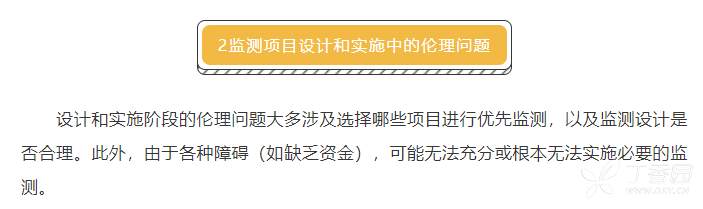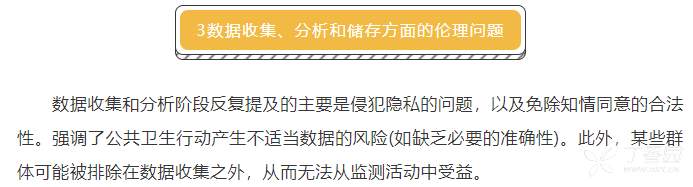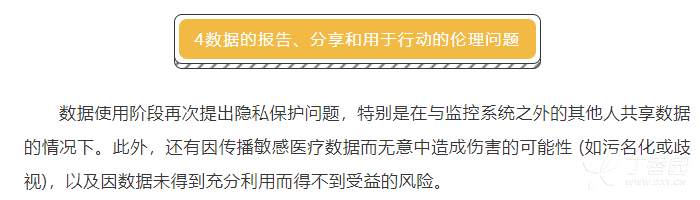公共卫生监测的伦理问题(转载)
公共卫生监测的伦理问题
原创: 巴璐 等 医学与哲学 今天
1.1关于选择公共卫生监测准则的问题
1.1.1因缺乏伦理准则而做出错误判断的风险
缺乏使用网络数据的伦理准则。公共卫生学界已经认识到互联网在公共卫生监测方面的潜力,通过社交平台,可以监测传染病的流行,及早识别疾病爆发、发现大规模人群聚集中疾病的爆发、认识和理解健康相关行为。尽管互联网监测具有明确的实用性,但人们对其在伦理上的适当性仍存疑虑,因为一个研究人员就可以自行处理数亿个公开信息。许多网络研究人员在大学计算机系工作,他们往往缺乏像医疗卫生人员那样应有的伦理意识[4]。
缺乏使用死者数据的伦理准则。很少有人考虑对死者的伦理义务,尤其在利用电子病历(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EMR)数据时,但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EMR上很大一部分信息与死前这一时期有关[5]。
1.1.2使用不当伦理准则导致错误判断的风险
采用公共卫生研究的伦理准则。因为缺乏区分“研究”和“监测”的标准,当公共卫生监测的常规工作被认为是以人群为基础的研究时,会阻碍对公共卫生威胁迅速有效的反应。因为“研究”必须经过伦理委员会审查,并且获得参与者的知情同意。
采用健康安全的伦理准则。公共卫生被认为是一个健康安全问题,当防治疾病成为打击人类敌人的战争,监测就显得异常重要,也更容易被接受并得到辩护,必要的伦理审查可能就会被忽视[6]99。
采用临床伦理准则。目前很多公共卫生监测采用的伦理准则主要引用和适用于临床医学。强烈地以个人为导向,并不一定适用于对人群的研究。例如,对乙肝病毒表面抗原的监测往往需要特定人群最大限度地参与,以便产生可靠的结果,并依此结果进行干预。
1.1.3与生成证据的科学标准有关的问题
不同知识体系之间存在冲突。尽管学界在不断更新、界定和规范有关传染病的认识,仍有许多人愿意探索新知识并提出新观点。在此过程中,相互竞争的观点常常被抹去或从属于未经证实的信念[7]。在预防性干预措施的前瞻性观察研究中,伦理限制会妨碍证据的形成和利用,这不可能仅靠科学来解决,而需要在社会层面就试验风险和受益的分配等问题进行广泛辩论[8]。
1.2公共卫生监测条件不足的问题
妨碍开发监测技术,以提高监测效率的风险。几乎所有投资者和技术开发者都只关注以个人为导向的医疗干预措施 (如诊断和治疗方法),极少去投资或开发以人群健康为导向的产品。开发和利用人群健康技术需要多学科协作,目前将监测新技术商业化的很少,因为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缺乏商业专长;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和企业家通常又不具备人群健康方面必要的专业知识。
没有足够有力的证据证明监测方法有效的风险。人们普遍认为,工业国家建立的所有传染病监测系统都会有最佳表现,事实上这一说法缺乏证据。对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的监测系统的评估是否应该参照发达国家的标准,目前仍存疑[9]。
2.1决定实施哪种公共卫生监测
2.1.1在不同公共卫生项目之间确定优先次序的风险
确定需要优先进行的公共卫生监测,首先要明确监测的公共卫生目的,以确保收集的数据适用于解决关键问题;还要根据影响的大小,以频率、严重程度、成本或可预防性来排序,确定需要优先解决的公共卫生问题[10]。
对单病种监测和其他公共卫生活动之间确定优先次序。例如,通过对急性弛缓性麻痹 (acute flaccid paralysis,AFP) 的国际监测,消除小儿麻痹症也能取得和消灭天花一样的成就。但在公共卫生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无论对单病种干预措施多么有效和适当,都需要支付公共卫生服务成本[9],与其他公共卫生项目争夺资源。
在潜在的新威胁和一直存在的现有健康问题之间确定优先次序。新发传染病的威胁总能引起极大的关注,2003年的非典就是一个例子,当前的热点是禽流感。但这种关注应在多大程度上分散决策者对主要地方病、卫生系统崩溃或专业技能严重短缺等持续的和“传统”的公共卫生事件的关注[8]?
2.1.2优先投资不适当的监测项目而浪费资源的风险
优先投资对发达国家重要的疾病领域,而不是某地区急需的领域。由于大量投资于监测新的潜在传染病,使得其他更急需投资的传染病(如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所得份额减少。2009年甲型流感病毒(H1N1)大流行,1年2个月内夺走了18 000条生命,虽然严重,却大约只相当于一周内死于疟疾的人数[11]。
优先投资较成熟的监测项目。美国和英国以及其他捐助国家曾因将更多的资金和活动集中在传染病控制和全球卫生方面而受到批评,因为这些投资和活动只针对几种特定的疾病或只通过垂直项目,而没有针对复杂、庞大的卫生系统建设以及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等疾病控制的基础[12]。
2.2公共卫生监测设计的适宜性问题
2.2.1在监测项目设计中确定优先次序的风险
在数据的全面性、准确性和监测的效率间确定优先次序。主动监测的数据往往更加全面,但比被动监测需要更多的资源。数字技术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和保护数据安全,优化效率,在不损害治疗的情况下节约治疗费用,如EMR。但所有的安全和隐私技术都伴随着相关成本,保护隐私和降低成本之间就存在着直接的冲突[5]。
在减少假阳性报告的情况下,尽量做到早发现或提高效率。越早监测,公共卫生信息就能越早指导决策。然而,越早监测,就越有可能报告“假阳性”,甚至是误诊[10]。
在尽量多地收集和使用数据还是为隐私安全而限制数据收集量之间确定优先次序。理想情况下,数据库中的任何个人都不可能被识别。然而,这限制了可以收集的信息量,影响了监测的有效性。因此,要权衡数据效用和隐私安全,以减少被识别的风险[13]。
2.2.2监测项目设计中的伦理风险
没有充分考虑监测中的公平问题。很多监测行为都存在从低收入和多族裔社区中过度取样的问题,因此我们将更有可能在这些社区发现更高的风险。研究者很少来自这些社区,未必了解这些社区的需求,以及他们的研究对居民的影响。低收入社区的人们受教育的机会较少,营养状况较差,对健康和疾病的理解也存在文化差异。这类社区也不太可能像白人社区,有居民自己就是科学家、医生、律师或其他专业人员,可以为邻居们解读数据;因此,低收入社区可能更难以主动,或者促使政府采取必要措施处理健康风险。
监测活动流于形式。比如在为患病风险最高的少数人群制定有针对性的筛查政策方面,官僚化固定格式的监测报告就不足以为公共卫生实践提供信息[14]。有时过分强调一致性,数据以统一的格式收集,可能会掩盖有环境特点的变量,从而排除了对当地有意义的监测结果[8]。
没有使用卫生信息新技术改进监测活动。信息技术在临床上运用得很好,从经验来看,信息新技术也可能极大地促进公共卫生[15]。
委托无能的、效率低下的或不道德的工作人员进行监测。资金流向和机制影响了数据的收集方式,在有些情况下,资金资助方指定的机构还不如其他机构更有效[16]。
2.3实施监测中的伦理问题
2.3.1监测项目的法律法规和管理结构不合理
不一致或过于复杂的法律或规范使有效和合乎伦理的监测措施复杂化,这使相关人员感到迷茫,担心正在进行的监测是否违背伦理[14]。
没有适合监测的伦理审查机制确保遵守伦理义务,特别是涉及在线数据源的项目。即使公共卫生监测是实践而不是研究,对公共卫生监测的伦理审查不必模仿现有的涉及人的研究的伦理审查,但对实名报告的公共卫生监测仍有必要进行更加系统的伦理审查和监督[6]103。
不同地区或部门的伦理委员会做出不一致和拖延的决定。不同的伦理审查委员会对隐私和伦理问题的解释和适用不一致,会拖延和阻碍监测项目。为使多中心研究获得及时和一致的伦理委员会批件,需要为研究制定更适用的审查程序[13]。
2.3.2妨碍成功实施监测项目的风险
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经费、技术、制度、人力资源)。《国际卫生条例》要求各国政府在地方、州等各级公共卫生机构实施和维持疫情监测。这对缺乏基础设施的欠发达国家来说是严峻的挑战[17]。在熟练的人力资源严重短缺,医疗部门面临巨大困难,而且多年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监测任务成倍增加却又协调不力,即使有配套资金,也很难获得更多的监测成果[9]。
《国际卫生条例》没有要求各国如何进行监测,却要求监测应该产生什么结果。尽管这为各国提供了很大的自由来确定符合国情的监测机制,但也可能导致被动的公共卫生报告制度,有时被动监测对早期发现传染病爆发是不敏感、不可靠的。
监测项目没有适当的和充分的保障措施。对传言的监测只有在为系统收集、核查和分析配备足够的人力资源后才有意义,因为大多数传言是虚假警报。特别在发展中国家,有关工作人员已经在管理官方监测报告方面不堪重负[9]。
公众没有参与监测项目的制定和实施。公众参与包括向公众提供信息,并根据公众价值观为监测活动辩护,因为公众的信任与合作至关重要。
缺乏政治、社会或机构的承诺。漠视结核病患者的社会状况,特别是迁徙者的生活条件,部分原因是整个社会无视卫生保健的不平等,造成迁徙者在寻求医疗服务时面临的困难[15]。
2.3.3监测系统的负担和效益分配不公的风险
发展中国家过多地负担了国际监测的任务。即使是根除天花或小儿麻痹症这样有明确效果的公共卫生行动,对资源贫乏国家的公共卫生服务也有相当大的风险。他们的监测系统脆弱,所需监测的新威胁又常常难以捉摸,加入全球性监测对他们破坏性影响大于所得到的好处[9]。
2.4与特定类型的公共卫生监测有关的其他问题
2.4.1过多关注基因而对其他潜在危险因素关注不足,易将责任转嫁给个人
基因中心论将DNA作为导致潜在健康和疾病的唯一原因,它不仅分散了人们对基因-环境和基因-基因相互作用复杂性的认识,而且倾向于完全忽视社会经济、文化和环境对疾病的影响,这趋向于进一步将疾病的风险归结于个体的生物学特点,即潜在的个人责任,进而造成社会、环境政策和医疗保健系统根据个人生物学类别进行资源重组[8]。
2.4.2实时监测系统的风险
监测对医疗卫生人员所依赖的EMR的可用性产生负面影响。由于很多监测依赖于EMR,这增加了EMR的负荷。在疫情爆发期间,同时执行的请求和相应的进程太多,会降低EMR的反应能力。
2.4.3大流行期间疫苗安全监测系统运行的风险
疫苗安全监测系统必须在疫苗使用过程中对其进行有效监测,但在大流行期间,疫苗需求量多、供应有限、常常需要在彻底评估疫苗安全性之前将疫苗分发出去,这就要平衡及时发现不良事件与疾病严重程度和疫苗效力问题[18]。
3.1保护自主权/隐私权的问题
3.1.1不知道数据的使用情况,也不知道可以选择退出
关于提前告知的问题包括:相关人群或个体可能看不到海报或传单,或者可能不理解其所含信息的意义。有些网站在一定程度上向用户提供量身定制的健康信息反馈,但他们与其他商业实体分享所收集的数据,消费者无法理解,甚至意识到自己的数据被用于监测、研究和其他目的[19]。
3.1.2故意违反隐私/保密规定的风险
非法机构要求的数据不合理。当无法获得数据主体的同意时,只有经过适当的法律授权,和正当的法律程序才能获得数据。但目前仍有参与数据处理的人未经授权发布数据。例如,曾有外国卫生部门官员向同性恋酒吧的顾客展示了载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姓名的名单[20]193。
3.1.3无意中违反隐私保密的风险
由于数据存储和传输不当,遭到未经授权的访问,尤其是在使用数字技术的情况下。例如,存有病人数据的电脑被盗,或被黑客攻击等。新技术方便了数据的收集和储存,但计算机数据的集中存储和容易获取大大增加了滥用这些信息的可能性,未来的发展可能会证明有必要对这些技术进行某种遏制。
另外,还有一些很难预测的威胁。涉及到误用系统的可能性,也涉及到监控服务用户界面的可用性,系统的设计必须保证不误发或不错发敏感信息,例如,当某地区疾病控制中心向该地区所有全科医生群发关于可能爆发流行性疾病的信息时,意外地发送给其他接受者。
3.1.4获取知情同意与实现公共卫生利益之间的冲突
特别是在基于实名或个人身份信息的报告中,未经患者明确同意的公共卫生监测的伦理辩护导致公共卫生伦理不同于临床伦理。伦理原则相互矛盾之处在于:一方面医疗工作者有保护病人隐私的责任,另一方面公共卫生机构有责任利用这些信息改善人群健康[10]。监测产生的数据有助于采取有效的公共卫生行动,但只要监测需要获得个人身份信息,就会威胁到个人隐私,并引发对缺乏或不重视个人知情同意的关注[6]101。
3.2为指导公共卫生活动提供的信息不适用的问题
3.2.1收集的数据不够准确或不够完整的风险
这些风险包括:从用户提供的在线数据源收集不正确/虚假数据;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不能正确或充分地使用数据收集软件,损害了数据的有效性;由于电子采集系统的软件错误或操作,降低了数据的有效性;仅从部分人群中收集的数据,无代表性。
3.2.2卫生专业人员不愿上报数据的风险
卫生专业人员不信任监测系统的合法性、可用性和隐私性。如果医生对监测的合法性有严重怀疑,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停止报告。由于担心医疗记录会伤害患者,医生可能不如实记录一些重大诊断和治疗。例如,为精神病患者做两份诊疗记录;临床医生使用“代码”以掩盖真实的临床记录。虽然可能有法律保护患者隐私,但只要患者或其医生怀疑记录不会长时间保持足够的私密性,那么这种保护仍然是不够的[5]。
在没有酬劳的情况下,卫生专业人员不愿承担监测任务。从为说服医生履行职责所做的持续努力可见,即使不是积极反对,某些医生也在抵制监测报告。因为报告需要时间和精力,而且往往是无偿劳动[20]13。
3.2.3对数据分析和解读不足或过度的风险
关于具体监测内容的证据空白妨碍了充分解读。对生物标志物的理解和概念往往存在着知识、数据和验证方面的空白,使解读变得困难;例如,缺乏许多无处不在的环境化学品及其代谢物的背景和基线值的知识[7]。
使用Meta分析和数据挖掘等计算工具可以很方便地解读数据,它从看起来混乱的数据中得出结论、答案或提供建议。但关于Meta分析本身在方法和可靠性方面仍存在争议。
紧急情况下的细致分析可能导致有害延误。处理数据可能会导致其发布延迟。某些数据收集程序规定必须经过彻底地清理和操作,才能保证所发布和解释的数据是正确的。然而,当数据能够公布时,对需要做出快速反应的事件,例如,防止传染病的传播,其公共卫生监测的价值可能就有限了[14]。
3.3数据收集中未充分考虑少数(弱势)群体的问题
3.3.1因不适当的数据收集策略,导致无视少数(弱势)群体需求的风险
基于网络的监测将那些没有互联网的人排除在外。数字鸿沟在世界范围内仍然存在,一些国家的互联网使用率非常低。基于网络数据的健康研究是否具有普遍性?是否存在偏倚?这是一个伦理问题,因为特定群体很可能不能从相关研究中获益。利用在线信息进行的卫生研究可以改善卫生政策,促进医疗进步,缺乏在线信息可能会加剧现有的卫生不平等现象[19]。
那些最有可能面临结核病风险的人——无证迁徙者和那些无法得到医疗保障的人被忽视了[15]。为了使数据涵盖所有的人群,每年至少应对每个家庭访问一次,对最贫困地区的家庭,应增加随访次数。忽视了有色人种的需求。应强调研究(包括作为研究的观察或监测)中标准的伦理要求。这些措施包括公平选择研究对象,避免忽视穷人或有色人种[6]101。
3.3.2只收集某些少数人群的数据,存在污名化的风险
特别针对迁徙者的策略。大多数有关结核病筛查的社会科学研究都侧重于将迁徙者作为高风险的群体,从而表明有针对性的结核病筛查在政治上是无辜的,而且与国家政治事务直接相关,尤其是涉及(边境)管控的政治事务。这些研究形成了加强对移民干预和监测的公共卫生政策。因此也给迁徙者贴上了高风险标签,使他们被污名化并在政治上被排斥[15]。
3.4与特定数据收集策略有关的问题
通过死因推测收集数据易引起受访者情绪的困扰,其痛苦程度取决于各种因素,如死者的年龄、与被访谈对象的关系、死亡情况、文化、死亡后的时间间隔以及访谈者的询问技巧[21]。这些因素导致访谈数据不可靠。访谈人员常常听到两种相互矛盾的死亡说法,一种来自死者的亲戚,另一种来自邻居。例如,亲属模糊地报告说是死于发热,但邻居报告的是艾滋病;亲属模糊地报告说是身体不适,邻居报告的却是自杀[22]。
无法告知患者的伦理风险。使用匿名的,无法与被监测对象关联的血液检测进行监测时,可能无法向病人告知疾病,并使他们失去治疗机会[23]。
4.1在数据报告和分享中充分保护隐私权/保密的问题
4.1.1故意违反隐私保护规定的风险
公共数据库一般应仅用于群体的利益。对公共数据库的潜在不当使用可能是为了某种私人利益。这不是批评自由化的市场制度,只是需要注意, 公共资源一般不应服务于私人利益。
4.1.2无意中违反隐私/保密规定的风险
发布数据的人没有受到过充分的数据保护方面的培训,导致不熟悉数据的法律和技术限制的人滥用数据;公开披露能够间接识别具体个人的数据;公开引用社交媒体信息[4];公开发布的与其他来源链接的数据可以识别具体个人[16]。
4.1.3保护隐私和共享数据实现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
比如与移民、福利或刑事执法部门共享数据。应在尽可能广泛地传播高质量数据和保护个人隐私之间取得平衡。
4.2标签化引发的危害或限制自由的问题
4.2.1造成身体、社会或情感伤害的风险
关于未经同意收集信息,和滥用所收集信息的风险主要是社会心理性质的——尴尬、污名化、就业困难等[6]101。可能死者不再具有伦理上的意义,尊重死者的依据是“不对活着的亲属心理造成伤害”,于是就产生了处理死者信息的实质性义务。死者为大,人们仍然希望死者的医疗记录保密,声誉不会受到影响[5]。
个人/社区遭遇经济上的负面影响。监测信息的公布,可能会导致强加的贸易制裁,造成不利的经济后果,比如对疫区产品进行禁运。
另一个可能的意外负面结果是,由于信息公布,有些医生会拒绝困难的、不顺从的病人,以减少麻烦[6]。
个人得不到可以保护其隐私的医疗。为了保护个人隐私,个人可能避免采取有利于其健康的行动,如艾滋病诊断或耐药检测。这不仅对个人有害,而且由于新感染和耐药病毒传播的增加,公共卫生也可能受到损害[24]。
4.2.2免受社会心理伤害与实现公共卫生利益之间的冲突
保护社区免遭污名化还是通过额外资助使其受益。虽然不可能消除弱势人群面临的所有风险,但利用数据帮助这些群体的好处可能超过有限或短期的危害。例如,报告某社区酒精和毒品使用率高可能给该社区带来潜在负担或耻辱,但也可能因此获得额外的药物和酒精治疗服务[25]。
4.2.3个人自由与实现公共卫生利益之间的冲突
个人/社区面临强制性干预或惩罚。结核病和性病之类传染性疾病常给患者带来巨大的道德羞辱,披露的后果可能是毁灭性的。虽然很少实施,但隔离威胁到结核病和性病患者的自由[26]。
实施有利于目标个人(病人)的强制性干预措施。在关于艾滋病的辩论中,强制性措施常使那些不仅因疾病而且因种族和阶级而变得弱势的人的生活受到不应有的侵犯。事实上,正是边缘化人群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才需要公共卫生的努力以填补巨大的缺口。
实施有利于其他个人(公众)的强制性干预措施。一个更特殊的例子是,受到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医疗人员在理论上存在着血液传播的风险,登记制度能否阻止他们对其他病人进行侵入性医疗。这为防止风险而限制了某些人自由的登记制度提供了辩护[26]。
4.3由于数据问题而影响公共卫生利益
4.3.1数据未被(及时)用于公共卫生行动的风险
缺乏根据数据结果采取行动所需的资源。例如,糖尿病监测项目收集的个人身份信息只用于患者的随访,由于资源限制,并不能为他们提供后续治疗[6]109。
优先于公共卫生目标的其他政治利益。有时中断对病人治疗的原因是政治性的,如对非法移民的结核病治疗因为其被驱逐出境而中断。中断治疗不是医生的错,也不是患者的错,而是受移民政策的影响。既然完成治疗在政治上是不可能,那么开始治疗就是在医疗上的不负责[15]。
4.3.2不与其他行为人共享数据的风险
国家保护阻碍政府间的数据共享。在非典和禽流感流行时期,有些国家出于国家保护,推迟或拒绝与世界其他国家分享疾病风险的信息[12]。
对自身知名度的政治兴趣阻碍了各机构之间的分享。数据管理者出于政治或历史原因或担心如果其他人能够访问其数据,他们项目的重要性或被关注度可能会降低,因此他们不愿意共享数据[14]。
对数据共享的投资不足。资源经常大量用在公共卫生监测的前期规划、数据收集和分析阶段,而对数据传播和转化阶段的投入比较少,这可能与资源不足有关。对数据共享的投资不足,使其更加得不到关注;如果加大对数据共享的投资,可能会促进今后的数据共享[14]。
处理数据的过程不一致阻碍数据共享。如果编码、格式、定义和方法不同,或随时间推移而改变,或数据以不兼容的格式存储,数据共享可能会受到阻碍,特别是对数据的一些趋势性分析可能会受到影响[14]。
4.3.3没有向公众充分宣传健康的风险
无意中没有提供所有相关信息以采取行动,这是沟通问题。出于政治原因故意传达误导性信息。这些不准确和误导的沟通破坏了人们对政府、公共卫生声明和公共卫生政策的信任。没找到适当的警报水平来引导公众情绪。无论是反应过度还是反应不足都很危险。
以上公共卫生监测中可能遇见的伦理问题,有些是常见的,普遍存在于各国;有些则是一些国家所特有的,并不具有普遍性。因为篇幅所限,很多问题没有详细描述。我国关于公共卫生伦理的研究不多,关于公共卫生监测伦理的讨论和研究更为鲜见,认识和借鉴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提高伦理委员会审查公共卫生监测项目的质量;也有助于从业人员在规划、实施和执行公共卫生监测时对需要考虑的各种伦理问题的理解,形成一套适合我国实际的公共卫生监测的最佳实践。

[1]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2005[M].3rd ed.Geneva: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16:1.
[2]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 Guidelines on Ethical Issues in Public Health Surveillance[R/OL].[2019-01-17].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255721/9789241512657-eng.pdf;jsessionid=74**CF4E776C08D8489BEAADF7A7B91B?sequence=1/.
[3]KLINGLER C,SILVA D S,SCHUERMANN C,et al.Ethical issues in public health surveillance:A systematic qualitative review[J].BMC Public Health,2017,17(1):295.
[4]CONWAY M.Ethical Issues in Using Twitter for Public Health Surveillance and Research:Developing a Taxonomy of Ethical Concepts from the Research Literature[J].J Med Internet Res,2014,16(12):e290.
[5]FAIRWEATHER N B,ROGERSON S.A moral approach to electronic patient records[J].Medical Informatics,2001,26(3):219-234.
[6]CHILDRESS J F.Surveillance and Public Health Data:The Foundation and Eyes of Public Health[M]//BERNHEIM R G,CHILDRESS J F,BONNIE R J,et al.Essentials of Public Health Ethics.Burlington:Jones & Bartlett Learning,2015.
[7]BRIGGS C L,NICHTER M.Biocommunicability and the biopolitics of pandemic threats[J].Med Anthropol,2009,28(3):189-198.
[8]SUSANNE B.Societal and ethical issues in human biomonitoring:A view from science studies[J].Environmental Health,2008,7(Suppl 1):S10-S10.
[9]CALAIN P.From the field side of the binoculars:A different view on global public health surveillance[J].Health Policy & Planning,2007,22(1):13-20.
[10]LEE L M,HEILIG C M,WHITE A.Ethical justification for conducting public health surveillance without patient consent[J].Am J Public Health,2012,102(1):38-44.
[11]NG E S,TAMBYAH P A.The ethics of responding to a novel pandemic[J].Ann Acad Med Singapore,2011,40(1):30-35.
[12]BARNETT T,SORENSON C.Infectious disease surveill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Kingdom:From public goods to the challenges of new technologies[J].J Health Polit Policy Law,2011,36(1):165-185.
[13]KOTECHA J A,MANCA D,LAMBERT-LANNING A,et al.Ethics and privacy issues of a practice-based surveillance system:Need for a national-level institutional research ethics board and consent standards[J].Can Fam Physician,2011,57(10):1165-1173.
[14]KEHR J.Blind spots and adverse conditions of care:Screening migrants for tuberculosis in France and Germany[J].Sociol Health Illn,2012,34(2):251-265.
[15]GOODMAN K W.Ethics,information technology,and public health:New challenges for the clinician-patient relationship[J].J Law Med Ethics,2010,38(1):58-63.
[16]BERNSTEIN A B,SWEENEY M H.Public health surveillance data:Legal,policy,ethical,regulatory,and practical issues[J].MMWR,2012,61 (Suppl 3):30-34.
[17]STURTEVANT J L,ANEMA A,BROWNSTEIN J S.The new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Considerations for global public health surveillance[J].Disaster Med Public Health Prep,2007,1(2):117-121.
[18]HODGE J G,Jr,GOSTIN L O,JACOBSON P D.Legal issues concerning electronic health information:Privacy,quality,and liability[J].JAMA,1999,282(15):1466-1471.
[19]VAYENA E,MASTROIANNI A,KAHN J.Ethical issues in health research with novel online sources[J].Am J Public Health,2012,102(12):2225-2230.
[20]FAIRCHILD A L,BAYER R,COLGROVE J.Searching Eyes:Privacy,the State,and Disease Surveillance in America[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
[21]CHANDRAMOHAN D,SOLEMAN N,SHIBUYA K,et al.Ethical issues in the application of verbal autopsies in mortality surveillance systems[J].Trop Med Int Health,2005,10(11):1087-1089.
[22]MONY P K,VAZ M.A qualitative inquiry into the application of verbal autopsy for a mortality surveillance system in a rural community of southern India[J].World Health Popul,2011,13(1):30-39.
[23]DATTA J,KESSELL A.Unlinked anonymous blood testing for public health purposes:An ethical dilemma?[M]//PECKHAM S,HANN A.Public Health Ethics and Practice.Bristol:Policy Press,2010:101-116.
[24]BROOKS J I,SANDSTROM P A.The power and pitfalls of HIV phylogenetics in public health[J].Can J Public Health,2013,104(4):e348-e350.
[25]HEILIG C M,SWEENEY P.Ethics in Public Health Surveillance[M]//LEE L M,TEUTSCH S M,THACKER S B,et al.Principles & Practice of Public Health Surveillance.3rd e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198-216.
[26]FAIRCHILD A L,GABLE L,GOSTIN L O.Public Goods,Private Data:HIV and the History,Ethics,and Uses of Identifiable Public Health Information[J].Public Health Rep,2007,122(Suppl 1):7-15.
最后编辑于 2022-10-09 · 浏览 5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