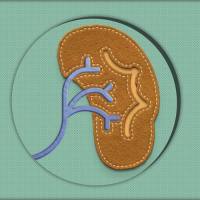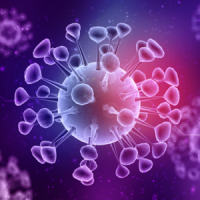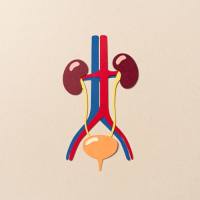“让医生摆脱被表述的命运”——读《文学双城记》有感
一
我向来是不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舆论的。然而这回竟颇出于我的意外:一是流言竟可以这般持刀,二是白衣竟可以这般流血,三是流血之后还要自己蘸着血在地板上写“我错了”。
二
医生们被围观了。 先是“围”,后是“观”。围的是手机屏,观的是猎奇眼。 于是,诊室里低声的解释,都被录成供词;沉默的摇头,都被剪成忏悔;来不及擦的汗,都被放大成“做贼心虚”。 他们成了“被表述”的物种——口不能自辩,手不能自书,只许在热搜的标题里活着:“黑心医生”“吸血医院”“惊天黑幕”。 若有微弱的自辩,便群起而咻之:“你拿红包时怎不发声?”——好像一个人若曾被疑指为贼,便终身无权喊冤。
三
舆论的刀法,是先立一块“高尚”的牌坊,然后逼你跪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动一动,便是“背叛了希波克拉底”; 喘口气,便是“吃了患者的血肉”; 若竟敢下班,便是“没有医德”; 若竟敢吃饭,便是“发国难财”。 总之,他们须得做圣人,而圣人是不许吃饭、不许喘气、不许有家的。 一旦跌下神坛——不,是跌下牌桌——便该万剐千刀。 神坛其实从来没有梯子,只有陷阱;牌子其实从来没有金字,只有钉子。
四
医院的楼梯拐角,一个年轻医生把白大褂脱下,翻过来,让里子朝外,放入包中,才敢走出去。 问其故, 他低声道:“怕被闹事的家属认出。”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阿Q进城的时节,也把辫子盘在头顶,生怕被人识破。 医生与阿Q,本隔着云端,如今却在同一条阴影里爬行。
五
舆论的配方,是九分开水,一分糖精,搅一搅,便叫“真相”。 于是报纸上说:“形势大好,群众获得感显著提升。” 电视里说:“集采砍价,百姓喜笑颜开。” 至于走廊里排长队的病人,至于值班室里合衣而眠的医生,至于那台因耗材断供而暂停的手术——皆不在镜头之内。 镜头只拍笑脸,笑脸只拍一秒;一秒之外,是十小时的沉默,是三十年的透支,是一纸“自愿加班”的空白协议。
六
有人说,他们也该自己开口,也该自己动笔,也该自己抢回被没收的声音。 然而,他们若开口,便是“诉苦”; 若动笔,便是“洗白”; 若举手,便是“群众对立面”; 若联名,便是“有组织抹黑”。 总之,他们只剩一条路:被表述,被剪辑,被盖章,被钉在“高尚”的十字架上,流尽最后一滴血,然后被拍照留念—— 照片下方,配一行小字:“大爱无疆”。
七
我不止一次听见人冷笑:“既做医生,便该认命。” 认命,认命,多少罪恶假汝之名! 认命便是让渡话语权,便是把白大褂改成囚衣,便是把听诊器改成锁链,便是把十年寒窗改写成“活该”。 呜呼!舆论的漩涡里竟有这般残酷的逻辑:你救人,你便该死;你救死,你便该杀;你若喊痛,便是罪加一等。
八
我要呼号,然而呼号也被“标题党”拿去当垫脚石; 我要控诉,然而控诉也被“热点”拿去做了背景音。 我只能写一点“毫无用处的文章”,给黑夜几个黑字:
——让医生自己说话!
——让诊室里的叹息,有机会盖过屏幕外的叫嚣!
——让手术刀的重量,有机会压过键盘的重量!
——让“被表述”变成“自表述”,让“被高尚”变成“自为人”!
九
倘若仍做不到,那么,愿中国青年医生,都学会两种语言: 一种是CT胶片上的沉默数据, 一种是深夜路灯下的低声怒吼。 前者救别人的命, 后者救自己的魂。
十
写到这里,窗外又起风。 风把一张破报纸拍在玻璃上,标题赫然: “医疗红利持续释放,群众满意度再创新高”。 我笑了笑,把报纸撕下,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 纸团落地,发出空洞的响声,像极了一颗心脏,被表述之后, 空余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