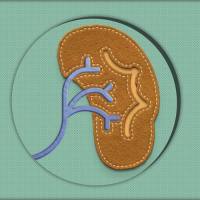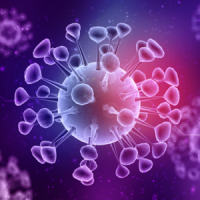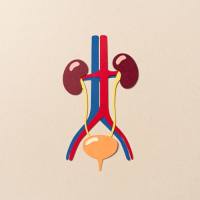第 34 轮长征疑难肿瘤MTB会议 | 罕见林奇综合征患者pCR后续治疗及BRAF融合肠癌靶向方
 caiwj2001 推荐
caiwj2001 推荐案例一
患者男,39岁。2023年3月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右下腹疼痛,程度剧烈,呈纹痛。于外院就诊提示“结肠占位伴系膜淋巴结增生”。
2023-07-26行全腹部CT平扫+增强检查示“1. 回盲部及盲肠管壁增厚并占位,伴周围肿大淋巴结,考虑肿瘤并淋巴结转移”,2023-07-27行结肠镜检查示“盲肠占位病变,大肠多发息肉”,快速石蜡切片病理示“盲肠中分化腺癌,结肠增生性息肉”。
既往无肿瘤家族史。2023-07-31来我科就诊,完善PET-CT检查,借当地穿刺样本行病理会诊及基因检测。
2023-08-02行第1周期新辅助化疗,具体为: 奥沙利铂 210mg 静滴 d1+希罗达 1.5g bid po d1-d14+贝伐珠单抗430mg 静滴 d1,q3w。
于2023-08-25、 2023-09-15 调整第2、3周期新辅助化疗方案,具体为: 奥沙利铂210mg 静滴 d1+希罗达 1.5g bid po dl-d14+ 信迪利单抗 200mg 静滴d1,q3w,辅以护胃、止吐等对症治疗。
于2023-10-13在全麻下行盲肠癌根治术,术后病理示:切缘毗邻:近切缘(-) 远切缘(-)基底切缘(-)。淋巴结转移:肠系膜淋巴结(0/9),最高群淋巴结(0/19)。
病理诊断:“右半结肠”在回盲瓣相应部位见一粘膜溃疡,其下肠壁内见大量粘液湖,经免疫组化标记,为缺乏上皮细胞被覆的粘液湖,未见明确癌组织。诊断:盲肠癌术后 腺癌 中分化 cTxN1M0 ypT0N0M0 ECOG 2。
于2023-12-01行第1周期辅助化疗方案(总第4周期),具体为:奥沙利铂210mg静滴 d1+希罗达 1.5g bid po dl-d14+ 信迪利单抗 200mg 静滴d1,q3w。
患者化疗不良反应不耐受,希望停止术后治疗。借术前穿刺样本,行MRD检测。
MRD检测结果连续阴性,暂停化疗,继续密切随访(3月1次MRD及影像学检查)。

基因检测结果

MRD监测及免疫组化结果
问题讨论
1. 患者是否确认为林奇综合征?
2. ctDNA-MRD在肠癌围手术期治疗中的意义?
分子生物学分析(王晶)
1.患者是否确认为林奇综合征?
患者免疫组化(IHC)结果显示错配修复蛋白MSH6表达缺失(-),NGS检测MSI-H,外周血白细胞检出MSH6 R922*胚系致病变异,提示该患者为林奇综合征(Lynch)。
该患者既往无肿瘤家族史,肠癌确诊年龄为39岁。既往报道林奇综合征(Lynch)患者发病年龄较早(中位44岁),是诊断的重要临床特征之一。然而家族史并非Lynch确诊的必要条件,以家族史诊断标准为依据,可能会漏诊20%~30%的Lynch阳性患者[1-3]。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4]对499名新诊断的连续结直肠癌患者进行分析,发现48.9%患者的家族史因记录不充分和/或患者不确定等原因存在不确定性。其中49名符合Lynch诊断标准。因此,对于携带有胚系MMR基因致病突变的患者,即使不满足临床诊断标准,也可诊断为Lynch。
2.ctDNA-MRD在肠癌围手术期治疗中的意义?
监控早期复发,指导辅助治疗:多项研究提示,早期肠癌术后或辅助治疗后MRD阳性预示更高的复发风险[5-7]。GALAXY研究[8]发现II期高危及III期术后MRD阳性患者能够从辅助治疗中获益,而MRD阴性患者观察与ACT预后无显著差异(图1),提示术后MRD阴性患者可考虑观察。分析术后4周和12周的ctDNA动态变化,发现二者ctDNA状态一致率为88.8%(744/838)。其中,持续阳性患者组6个月DFS率仅为58.3%,而“阳性->阴性”组6个月DFS率为100%,有显著提升。

图1 GALAXY研究中术后4周MRD+和MRD-人群接受不同辅助治疗疗效
DYNAMIC研究[9]是首个基于MRD指导结直肠癌患者术后辅助治疗的前瞻性干预性随机对照试验,其中ctDNA指导组和标准治疗组接受化疗的比例分别为15%和28%,相应的3年RFS率无明显差异(92.4% vs 91.7%,HR=0.96)。证实基于ctDNA指导的策略比标准治疗可减少辅助治疗应用,并且不影响复发风险。
预测新辅助治疗疗效:Tie等在2023 ESMO上对比了多项肠癌新辅助研究结果(图2),这些研究采用了不同的ctDNA assay进行疗效观察。结果显示大多数TME(全直肠系膜切除术)术前ctDNA-组都比ctDNA+组有更高的pCR率和RFS,提示Post CRT/TNT ctDNA能够预测直肠癌新辅助治疗后的反应。

图2 比较不同研究中ctDNA预测直肠癌新辅助治疗的反应
另一项研究[10]纳入了来自多中心II/III期随机试验的60例局晚期直肠癌(LARC)患者,同时收集这些患者的组织和血液样本,并采用3种不同的cfDNA检测策略:个性化panel、FIX-panel和基于拷贝数改变的低深度测序(CNAs)。结果表明,基于个性化分析的MRD阳性与复发风险增加显著相关(HR = 27.38;log-rank P < 0.0001)。而FIX-panel和CNAs在预测复发方面表现不佳(HR = 9.24; log-rank P = 0.00017)。此外,LARC新辅放化疗后通过ctDNA分层较临床和病理分层更优(RFS HR 27.38 vs 2.55)。
在其他癌种如肺癌中已有多项研究(Checkmate816,AEGEAN,CTONG1804等)[11-13]提示新辅助治疗后ctDNA清零与更高的病理学完全缓解(pCR)率相关。Checkmate816研究ctDNA清除的患者中纳武利尤单抗(Nivo)联合组和化疗组pCR率分别为46%和13%,而ctDNA未清除的患者中,Nivo联合组的pCR率为0。一项研究[14]收集了参加I-SPY2临床试验的84例高危早期乳腺癌患者291份纵向监测血浆样本,中位随访时间4.8年。发现在基线T0时ctDNA阴性或后续清零的患者DRFS(远处无复发生存率)显著长于治疗后ctDNA未清零的患者。更重要的是,新辅助治疗后ctDNA阴性但non-pCR的患者DRFS与pCR患者相当(图3,HR: 1.4(0.15-13.5))。

图3 ctDNA清零预示更好的远处无复发生存率
指导器官保留选择:对于经新辅助放化疗后实现临床完全缓解(cCR)的直肠癌患者,经过近20年的广泛临床实践,观察等待(W&W)策略已逐渐被接受[15]。然而,对于PD-1治疗后的MSI-H/dMMR结直肠癌患者而言,这种豁免手术的W&W是否可行仍处于探索阶段。免疫治疗后cCR的评估、获益于W&W策略的最佳人群仍有待进一步研究。2023年ESMO的一项研究[16]指出,新辅助治疗后ctDNA清零的患者有较低的远处转移风险,但是Non-pCR率仍然很高,结合cCR或可进一步指导肠癌患者选择器官保留(图4)。

图4 cCR+MRD或可指导肠癌患者选择器官保留
3. 后续治疗建议及总结:对于Lynch肠癌患者的全身治疗方案,依据《中国家族遗传性肿瘤临床诊疗专家共识,2021》可暂时参照MSI-H/dMMR表型患者诊疗方案执行。结肠癌NCCN指南(2024)指出,对于新辅助治疗后的dMMR患者后续治疗可以选择:①手术±IORT或②系统治疗或③观察。
考虑到该患者来我科就诊后化疗意愿强烈,临床给予充分新辅助治疗。手术后惊奇发现原发灶肿瘤完全消失,达到了pCR。行1周期辅助化疗后患者出现不耐受,希望停止术后治疗。
后续治疗建议如下:
- 继续定期随访观察,同时进行MRD监测及影像学等常规检查。若MRD转阳可综合考虑是否要给予再次辅助治疗。
- 若后续疾病进展,直至发生疾病转移或不可切除,可参考右半肠癌进行系统治疗。
临床团队分析和方案选择
焦晓栋教授:该患者考虑新辅助治疗是在多种巧合因素作用下的结果。若非如此,可能会选择直接手术切除。比较惊喜的是经过3个周期化疗后肿瘤实现了pCR。患者在完成一个周期辅助治疗后表现出停药意愿,由于缺乏充分的证据支持,对此临床判断也具有一定挑战。于是希望通过MRD检测给予一定提示。今年的肺癌高峰论坛其实也提到了所谓的适应性治疗,其核心就是关于MRD检测对于治疗策略的指导。在经与患者充分讨论后最终选择了降阶治疗。现在患者仍在观察随访中。未来希望MRD检测能够给类似的患者带来更多的指导。
秦保东教授:我们在复盘该病例时也感觉十分神奇。首先,如果这个病人来了直接开刀,是不是会有很好的效果?传统分期较早的肠癌患者是不做新辅助治疗的。若直接开刀,推测该患者术后至少是一个II期高危,因为已有淋巴结转移。但同样面临着术后如何选择的问题。且此时MRD可能不是阴性,患者可能也无法实现pCR。第二,考虑到病人是年轻的Lynch患者,可能治疗方案和传统的治疗方案不完全一样。第三,对于pCR的病人后续辅助治疗该怎么选择,也是我们纠结的一个因素。在没有MRD检测时,对于II/III期肠癌可能要按照高危因素进行术后辅助化疗。但当时仅仅针对的是化疗,那么免疫治疗后该如何选择?如今肺癌新辅助免疫治疗后的pCR率高达40%,使得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但从Keynote-671、Checkmate77T等研究数据可以看出,pCR的患者接受辅助免疫治疗后相比未接受治疗的患者生存并未得到改善,也侧面反映了做适应性治疗的可行性。
臧远胜教授总结:前面两位医生总结的非常好,对于该病例临床总结如下:第一是关于偶然性,在临床上好的治疗结果存在一定偶然性,欢迎这样的偶然性多多益善。第二,MRD到底能不能完全反映临床当中真正的pCR,还有一些问题要探讨。现有的研究告诉我们如果新辅助治疗后MRD阳性,大概率是会有肿瘤细胞残留的;而MRD是阴性不代表一定没问题。pCR更多代表肿瘤局部的反应,而MRD能从分子水平反映患者的全身状况。因此,二者结合可能是一个双保险,这合情又合理。今年的肺高论坛讲到了适应性治疗,非常赞同应该基于分子水平监测去选择适应性治疗的结论。第三,我们有很多创新的治疗或研究,其实都是借鉴了不同瘤种的“他山之石”。来自其他癌种的研究可能会给我们日常的科研思路带来重要的启示,也让我们敢于在临床实践中去尝试,应努力发扬光大。
案例二
患者男,65岁,2021年10月,腹部增强CT显示乙状结肠占位,胸部CT平扫显示右肺下叶内基底段、左肺下叶外基底段结节,考虑恶性、转移。2021年10月:行腹腔镜姑息性乙状结肠切除术,术后病理为中分化腺癌,pT3N1cMx。2021年11月,FOLFIRI+西妥昔单抗治疗5周期,2022年4月9日改为1日方案,期间行肺转移介入手术。2022年9月12日,因体力耐受性差更换化疗方案:雷替曲塞+西妥昔单抗。2023年1月疗效评价为PD,改变治疗方案为:雷替曲塞+贝伐珠单抗+奥沙利铂。2023年4月,再次疗效评价为PD,外院行放疗并予以瑞戈非尼 (患者家属因不良反应不考虑免疫治疗)。2023年11月,更换治疗方案为:TAS102+贝伐珠单抗。2023年12月19日外院腔内灌注贝代珠单抗。2024年1月,疗效评估PD,更改治疗方案为:瑞戈非尼+派安普利。2024.03评估SD,因派安普利过敏,维持单药瑞戈非尼治疗, 现寻求进一步诊治。
基因检测结果:为寻求精准治疗,患者接受了733基因NGS检测,结果显示受检肿瘤组织存在BRAF融合,FGFR1拷贝数增加,PIK3CA、LRP1B、TP53、ZNF703突变;MSS。

讨论问题
1. 患者未检出RAS突变,检出BRAF重排,是否影响EGFR抑制剂的获益?
2. BRAF重排有无BRAF抑制剂、MEK抑制剂获益可能?
3. FGFR1拷贝数增加有无用药机会?
4. PIK3CA突变用药方案探寻?
分子生物学分析(分子生物学专家高宁)
1. 患者未检出RAS突变,检出BRAF重排,是否影响EGFR抑制剂的获益?
BRAF融合导致BRAF蛋白的N端CR1自抑制区域断裂,无法有效抑制BRAF蛋白活化,导致BRAF基因形成二聚体而结构性持续活化,这种功能类似于II类突变[1]。有病例报道显示BRAF融合结直肠癌患者可从EGFR抑制剂中获益,一例左侧结肠癌患者术后辅助化疗2年后疾病复发,并出现淋巴结和卵巢多发转移。患者一线接受FOLFIRI+贝伐单抗治疗治疗,3个周期后CT显示淋巴结转移灶和卵巢转移灶增大。手术样本未检出RAS/RAF突变,检出EXOC4-BRAF融合。患者后接受了FOLFOX6+帕尼单抗的二线姑息化疗。六个周期后,患者达到PR,卵巢转移、淋巴结转移和大量腹水减少,肿瘤标志物也减少。12 个月以来,患者继续接受 FOLFOX6 +帕尼单抗治疗,最佳疗效为PR[2]。
2.BRAF重排有无BRAF抑制剂、MEK抑制剂获益可能?
基础研究显示BRAF抑制剂维莫非尼仅能降低BRAF V600E 诱导的 ERK1/2 磷酸化,但是曲美替尼可同时有效降低BRAF V600E和 PAPSS1-BRAF融合表达细胞中的 ERK1/2 磷酸化[3]。其他实体瘤的病例报道显示MEK抑制剂对BRAF融合的肿瘤有效,一例女性黑色素瘤患者携带ZKSCAN1-BRAF融合,口服曲美替尼治疗后出现了良好反应,14天内皮下肿瘤结节显示明显临床反应,右侧肺转移瘤的主要肿块在第45天显示出显著反应。此转移灶之前不可切,治疗后成功切除[4]。NCCN指南建议曲美替尼可用于携带BRAF融合或非V600突变的恶性黑色素瘤患者的二线及后线治疗[5]。一例肺腺癌患者检出SND1-BRAF (S10:B9) 融合阳性,在经多线治疗后,再次检测检出SND1-BRAF (S10:B9) 和BRAF-RNF150 (B8:R2) 融合。该患者接受曲美替尼1周治疗后,咳嗽明显缓解。4个月后,CT扫描证实患者获得PR,肿瘤缩小57%。截止文章发布仍在持续接受曲美替尼治疗[6]。BRAF V600E抑制剂对BRAF融合似乎没有作用,有病例报道显示BRAF融合可能与BRAF V600E黑色素瘤维莫非尼获得性耐药相关[7]。目前在结直肠癌中针对BRAF融合的靶向治疗还尚未有研究涉猎。
3.FGFR1拷贝数增加有无用药机会?
有小样本的研究显示,FGFR1扩增结直肠癌患者从佩米替尼中难以获益,14例FGF/FGFR变异的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接受FGFR抑制剂佩米替尼的后线治疗,其中8名经血液检出FGFR1扩增,ORR率为0%(95% CI,0-23.2%)[8]。FGFR1扩增对包含FGFR靶点的泛靶点激酶抑制剂有一定敏感性,一项研究在76名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中分析了FGFR1扩增与瑞戈非尼疗效之间的关系,76 名患者中只仅3名 (3.9%) 检测到FGFR1 扩增,而这3名患者均对瑞戈非尼实现了PR[9]。包含FGFR靶点的泛靶点激酶抑制剂有瑞戈非尼、尼达尼布、仑伐替尼、普钠替尼、帕唑帕尼、安罗替尼、卡博替尼、德立替尼、多韦替尼等。
4.PIK3CA突变用药方案探寻?
一项回顾性研究中,纳入54例结直肠癌患者,其中9例携带PIK3CA突变(17%)。6例结直肠癌PIK3CA突变患者接受基于mTOR抑制剂或PI3K抑制剂的治疗方案,其中四名SD,2名PD[10]。TAPUR研究共纳入了10例携带PIK3CA基因突变的CRC患者接受mTOR抑制剂坦罗莫司(temsirolimus)单药治疗,未观察到有缓解的患者,ORR为0%[11]。一项研究纳入39例转移性MSS CRC患者接受PI3K抑制剂可泮利塞(Copanlisib)与纳武利尤单抗联合后线治疗,共分为两个队列:队列1为PIK3CA突变型(PIK3CAm:22例),结果3例患者(14%)获得PR,3例患者SD(1.7-4.7个月)[12]。综上,目前PIK3CA突变尚无疗效较好的针对性方案。
临床团队分析和方案选择
王湛教授:结合患者的临床特征和基因检测结果,这个患者的后线治疗选择了曲美替尼+西妥昔单抗方案,但是患者的基础情况较差,感染也比较严重,同时患者类器官培养提示对吉西他滨和顺铂敏感,给患者上了小剂量的吉西他滨,当用药3周左右时,还没等到药物见效患者就去世了。
秦保东教授:本例患者是一例多线治疗后难治性肿瘤的典型代表,基因检测结果显示患者携带BRAF融合,FGFR1拷贝数增加,PIK3CA突变等很多突变,在既往的临床中BRAF融合相对罕见,与BRAF V600E突变不完全一样,它对西妥昔等EGFR单抗有一定的敏感性,跟我们上一期MTB提到的KRAS扩增与KRAS突变不同。治疗组也针对BRAF融合这个点进行了治疗,但是可能由于患者本身的状态差且合并突变较多,导致没有显示出疗效。对FGFR1扩增,我们既往也进行过佩米替尼的尝试,疗效似乎不太显著。PIK3CA突变在胆管癌、乳腺癌中也经常见到,从刚才的分析中,mTOR抑制剂+免疫可能也是一个备选方案。
臧远胜教授总结:这例患者是一个典型的常见肿瘤,经过多线治疗后,陷入无药可用困境的案例,对这类病人进行基因检测,通过MTB来寻找新的靶点是一个重要的路径。此外,这例患者基因检测结果发现携带很多基因变异,我们需要对这样的基因变异进行区分,这个患者主要有3大类变异:BRAF融合、FGFR1扩增、PIK3CA突变。我们在7、8年前就针对PIK3CA突变使用过依维莫司等mTOR抑制剂,但是往往结果是疗效很小但副作用很大,今天生信分析也再次告诉我们,目前在PIK3CA这条通路上的靶向药还是没有一个很好的疗效,包括PIK3CA抑制剂联合纳武单抗的研究也仅显示出14%的客观缓解率12,但是本身在晚期的肠癌患者中,单独的纳武单抗就有10-20%的有效率,所以没有办法判断PIK3CA抑制剂有无疗效加成,PIK3CA肿瘤驱动作用的大小还是有待考虑。目前已经获批的靶向药主要针对FGFR2靶点,并且一些基础研究中也论述了FGFR2变异是一个强的肿瘤驱动因素,但是很少提到FGFR1,同时这些获批的靶向药对FGFR1基因扩增等变异的疗效也并不好,所以它的驱动作用可能也不大,不同的是瑞戈非尼是肠癌中已获批的药物,同时包含了这个靶点,因此后线治疗时可以作为一个联合用药的选择。BRAF融合类似BRAF II类变异,与BRAF V600E不同,BRAF抑制剂治疗的疗效并不好,对MEK抑制剂有一定疗效,MEK是BRAF下游的重要调控因子,同时研究显示双靶联合的治疗模式也并不能带来更多获益。最后,类器官培养提示肿瘤对吉西他滨和顺铂敏感,一方面这两个药物并不是肠癌常用的方案,另一方面对经过多线治疗的状态较差的患者,后线化疗可能弊大于利。综合分析,这个患者如果有机会选择曲美替尼±瑞戈非尼,可能获益的概率更大一点。
最后编辑于 2024-09-04 · 浏览 2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