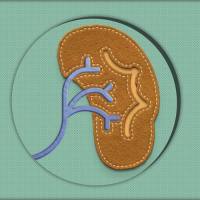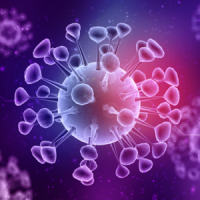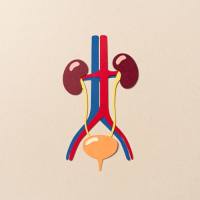前后有别,各有意义——心脏前、后负荷指标评估
引 言
转眼间血流动力学监测系列课程已经来到了最后一期。在前五期的内容中,我们从监测技术(无创、有创)、实施手段(补液试验、被动抬腿试验、心肺相互作用)、衍生指标(心功率、氧供)等多个维度解析了心排量(CO)。在课程的最后一站,我们将解构心排量的两大影响亦或是贡献因素——前负荷与后负荷。在液体反应性评估中前负荷的临床意义已经可见一斑,事实上,临床上影响前、后负荷的因素纷杂,因而赋予了两者各自的评估价值。
心脏后负荷及临床监测指标
心脏后负荷的概念借鉴了骨骼肌后负荷的界定方式——阻碍肌小节收缩总力-静息态肌小节拉伸力,可以理解为肌肉完成收缩需要克服的阻力。相应地,心脏后负荷为心脏泵血需要克服的阻力1。以左心室完成的体循环为例,它需要克服从主动脉到右心房的阻力,即总左室后负荷2:

可以理解为,左室后负荷=总外周阻力 (Total Peripheral Resistance, TPR),TPR也被称为外周血管阻力 (Systemic Vascular Resistance, SVR)。直接测定TPR难度较大,但如果我们将其类比为电阻,套用欧姆定律——电阻=电压/电流,电压对应心脏泵血产生的压力,电流对应心排量,可以得到:
TPR= 80 (MAP-RAP)/ CO (1)
注:MAP (Mean Arterial Pressure) 平均动脉压, RAP (Right Atrial Pressure) 右心房压力,80为用于单位换算的系数
TPR正常范围3为800-1200 (dyn·s) /cm5。如果将CO体表面积标准化,即使用心指数 (CI) 替代CO带入公式 (1),则可得到TPRI,正常值约在1700~2600 (dyn·s) /cm5·㎡2。
导致TPR发生异常变化的临床因素众多,可结合CI等其他临床指标进行具体分析4:
1. TPR降低:常见于药物影响、脓毒症等
低血压是全麻或脊椎麻醉等常见的副作用,TPR明显降低是主要诱因。对于老年人群而言,本身伴随着动脉顺应性的下降,麻醉剂造成低血压更有可能造成心肌缺血等较为严重的临床事件。一项连续纳入60例>80岁接受髋关节骨折修复术的日本回顾性研究5显示,在蛛网膜下腔麻醉过程中,对比发生或不发生低血压的患者,CO并未发生显著变化;相比之下,发生低血压患者组,蛛网膜下腔穿刺后20分钟内观察到TPR下降的患者比例显著高于未发生低血压患者。该研究提示,脊柱麻醉患者接受TPR补充监测以及时明确TPR的下降,对于预测低血压风险具有积极意义。

除了CO变化外,TPR下降、低血压是脓毒症患者典型的血流动力学改变。然而, CO的变化可能会被心率、后负荷等因素掩盖,因而结合分析TPR可能得出更为准确的预后评估结果。 一项纳入42例脓毒性休克患者的荷兰回顾性研究6对此进行了探讨。该研究对比了生存与死亡结局的患者,发现两组患者基线TPRI相近,但死亡患者组治疗期间TPRI谷值显著低于生存或者组;相比之下,无论基线或是谷值,两组患者CI均无显著差异(如下表)。

无独有偶,另一项中国前瞻性研究考察了基于TPR衍生的另一项指标——后负荷相关心脏性能 (Afterload-related Cardiac Performance, ACP)对于脓毒症患者的预后价值。ACP代表着实际测量 CO与预测CO(基于TPR,数值=394.07×TPR -0.64 )的比值。研究发现,ICU收治第3日,以APC≤78.1%作为cut-off值预测28日死亡风险,灵敏度、特异性分别为92.6%、92.9%,ROC AUC 0.976,预测准确性良好。
2.TPR升高:常见于心力衰竭、心源性休克等
心脏后负荷可出现急性与慢性升高,前者常见于急性充血性心衰、心源性休克等心脏疾病,而慢性升高常见于主动狭窄、持续性高血压等。如前所述,TPR的计算基于CO,两者存在偶联,因此TPR的急性改变结合CO相关指标可用于严重心脏疾病患者预后评估。Cotter G等人研究4发现,与健康人群相比,急性充血性心力衰竭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CHF) 患者、心源性休克、高血压危象、肺水肿患者TPRI存在不同程度升高,其中以肺水肿升高幅度最大。

结合心脏做功指数 (CPI)的变化特征,研究者勾勒了各类危重症人群的血流动力学特征分布谱:

前负荷—无创时代的监测与应用探索
心脏前负荷衡量心脏舒张末期心室的牵张程度,主要受静脉张力及循环容量的影响。前负荷病理性升高常见于心衰、二尖瓣狭窄、二尖瓣反流等;而脓毒症、大出血等导致分布性或低容量性休克常导致前负荷显著降低。肺毛细血管楔压 (Pulmonary Capillary Wedge Pressure, PCWP) 是评价前负荷的经典指标,但需要实施肺动脉插管8。在无创血流动力学监测时代,以胸腔液体容量 (Thoracic Fluid Content, TFC) 登上历史舞台。
1. TFC:利用胸腔电阻抗技术测得的心脏前负荷指标
顾名思义,TFC=胸腔血液+胸膜腔内液体+肺间质内液体,在无胸腔积液时,胸腔内血液是主要组成部分,且随心脏搏动发生周期性变化9。考虑到循环容量是心脏前负荷的重要决定因素,因而TFC顺理成章地成为前负荷的衡量指标。
将胸腔设定为一个电导体,其中的液体越多越容易导电,也就是电阻越小。早期使用胸腔液体指数 (Thoracic Fluid Index, TFI)的概念来定义胸腔电阻Z0,因此TFI与胸腔液体实际含量成负相关10。为了更为直接地反映胸腔液体量,化“负相关”为“正相关”,使用1/Z0 来定义TFC定义为。为了方便计量,引入校正系数1000,即:
TFC= 1000/(1000×Z0), kΩ-1 (2)
例如Z0=25 Ω,带入计算并转换单位,TFC=40 kΩ-1。11
提到TFC,可能会联想到另一个类似的指标——血管外肺水 (Extra-Vascular Lung Water, EVLW)。有别于TFC,EVLW仅反映肺间质内液体含量,因而多用于指示肺水肿状态。两者间比较详见下表。

2. TFC的临床评估价值
(1)联合CO辅助容量状态评估
如前所述,TFC可综合反映胸腔内循环血量、胸腔积液及肺间质水分,因而可结合CO综合判断容量状态,并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见下表)15:

(2)用于急性呼吸困难快速鉴别诊断
呼吸困难作为急诊最常见的症状,其主要病因可分为心源性与肺源性,两者症状高度相似,常规的超声心动图、胸部X光、放射性血管造影等鉴别诊断手段在急诊中难以实施14。一项美国前瞻性、观察性研究15,纳入45例急诊收治的呼吸困难患者,利用生物电阻抗技术Starling快速检测TFC,以明确呼吸困难是否由急性失代偿心衰 (ADHF)所引起。研究发现基线TFC≥78.8/KΩ 用于ADHF鉴别诊断准确性、灵敏度分别为76%、71%,ROC AUC 为0.81,准确性高于既往急诊医师经验性诊断(AUC 0.74)。
值得一提的是,心指数CI也被证实在肺源性与心源性呼吸困难患者中存在显著差异:通过体位变化(坐位至仰卧位),哮喘/COPD相关呼吸困难患者δCI变化显著高于心衰相关呼吸困难患者16。提示TFC可与CI联合,提升急诊呼吸困难患者鉴别诊断的准确性。
(3)指导术中液体管理
由于TFC可综合指示胸腔血液循环、胸水、肺间质水含量,一些临床研究同样将TFC用于容量评估探索。在血透患者中的研究17证实,TFC与透析清除水分存在良好的相关性:TFC减少1/kΩ相当200ml水分的清除。
循着该思路,一些研究试图TFC用于更多具有容量评估需求的临床情景中,如术中液体管理。一项韩国的前瞻性、观察性研究18纳入80例先心病患儿,采用Starling监测TFC、TFCd0(较基线相比TFC的变化率)等血流动力学参数。研究显示,TFCd0与术中液体平衡、术后体重增长均具有显著正相关性(如下图):



该研究初步验证了TFC监测用于围术期液体管理的可行性。
“瞻前顾后”:前、后负荷结合,指导危重症临床决策1
如下图所示,血压是危重症患者血流动力学特征最表层的反映,而CO是维持正常血压的前提。后负荷可直接影响血压,由可与前负荷、心肌收缩力共同影响CO影响血压水平。因此在危重症患者的临床血流动力学监测中,以更精细的颗粒度进行评估,即针对前负荷、后负荷水平制定针对性的干预策略,是改善患者临床结局的合理思路。

更多内容,戳此处关注百特医学时空进行学习~
参考文献
1. NCBI Bookshelf: Physiology, Afterload Reduction, LaCombe P, et al. , Updated on Apr. 24th, 2023.
2. 李文志, 等. 麻醉学(第 4 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3. 王天龙等,围术期肺动脉导管临床应用指南(2020版)
4. Cotter G, et al. Eur J Heart Fail. 2003;5(4)+443-451
5. Nakasuji M, et al. J Clin Anesth. 2012;24:201-206
6. Groeneveld ABJ, et al. Intensive Care Med. 1988;14+141-147
7. Zhao CC, et al. Medicine (Baltimore). 2021 Sep 24;100(38):e27235.
8. NCBI Bookshelf: Physiology, Cardiac Preload. O’Keefe E, et al. Updated on Sep. 26th,2022.
9. Hammad Y, et al. J Clin Monit Comput. 2019;33:413-418
10. Jewkes C, et al. Br J Anaesth. 1991 Dec;67(6):788-94.
11. Van de Water JM, et al. Am Sur. 2005;71(1)+81-86
12. Jozwiak M, et al. Ann Intensive Care. 2015;5:38.
13. Tagami T, et al. Curr Opin Care. 2018;24(3): 209–215
14. 张海峰, 等. 中国急救医学. 2008;28(9):781-784
15. García X, et al. Chest. 2013;144(2):610-615.
16. Engineer RS, et al. Am J Emerg Med. 2012;30(1):174-180.
17. Kossari N, et al. Hemodial Int. 2009 Oct;13(4):512-7.
18. Kang WS, et al. J Int Med Res. 2012;40:2295-2304.
最后编辑于 2024-04-22 · 浏览 3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