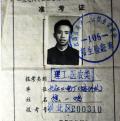以证统病研究的可行性探索
以证统病研究的可行性探索
焦一鸣
“以证统病”,是以证为中心,将各种病归纳在证之下,研究证的发生、发展及治疗后的转归,并探讨证与病的诊断和疗效关系。通常的做法有:“以证统中医的病”和“以证统西医的病”。我们提倡的是“以证统西医的病”,简称“以证统病”。
1.“以证统病”的背景 中医是以辨证论治为主,既往中医是以中医的病来统证,自从现代医学引入中国后,人们习惯以西医的病来统证,在一个病之下,分为多个证型,简称“以病统证”。这种将中医的证,分割在病之下,进行研究,破坏了中医证的整体性和完整性,不利于中医事业的发展。因此有学者认为[1]:这种方法使证的研究局限化,脱离了证的普适性和包容性,对证的认识容易套入西医疾病研究的思路,因而提出“以病统证”和“以证统病”同时进行。还有人提出[2 ]:为了保持中医学术的特色,希望“以证统病”,把中医的证放在统领的位置上,使其保特自主发展的势头。更有学者认为[3]:几十年来中医学未发生质的飞跃,未能形成独特的医学体系,大部分是停留在将西医的研究方法套用在中医上,因而提出要“以证统病”,探讨相同证候见于不同疾病中的同中之异,从同证异病的差异中寻找针对性强,能阻断疾病发展的有效方药。
2.“以证统病”的现状及内容 “以证统病”当前没有受到中医及中西医结合学术界的重视,表现在除了中西医结合学会有针对血瘀证而设立的“活血化瘀专业委员会”外,未见有以证为研究的学术专业组织,更无相应的以“证”为研究的相关临床科室。也无相应的以证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业刊物。这一切说明“以证统病”的研究没有进入中医的主流,以至于中医发展受到影响。
“以证统病”虽然目前有运用,但都未对其进行实质性的研究,一般都作为异病同治看待,如:用热炎宁颗粒治疗同属风热证的化脓性扁桃体炎、急性气管炎—支气管炎、单纯性肺炎 [4 ];以滋肾息风,治疗风阳上扰的各种老年脑病[5]。有的运用在中成药的新药研发 [ 6 ]及传统中成药的研究中,如:六味地黄丸用于治疗各种疾病的肾阴虚证,并认为“以证统病”符合中医药的传统特色和优势。还有的是作为中医诊断方面的探讨[ 7 ] 。在血瘀证的研究中,是“以治则统病”进行研究,与我们所说的“以证统病”还略有不同。
目前证候学的研究主要还是停留在研究证的概念、规范化、标准化、证的实质以及证在现代医学病中的分布规律和演变规律等方面,但都未有实质性的突破。而“以证统病”是证候学的一部分,他是研究证的发生、发展、变化以及证与病的各种关系的学科。我们知道在同一证候中,对不同的病,虽然治则相同、方药相同、疗效却不同;这是因为各个病有其不同的特异性。因此临床工作中,既要注意病的个性,也要注意病的共性[ 8 ]。还有的认为[ 9 ]“以证统病”要解决:证同病异而治不同,证同症异而治不同,证同病症不同而治不同,同证有轻、中、重之别,故而治不同的问题。
在辨证论治中,最后要落到证候上,证候是立法、选方、用药、论治的对象,因此证候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对证候的治疗研究。而且证具有可变性,它是以正邪盛衰变化为主导,导致有寒热虚实的变化;经治疗后,证候可由里出表;误治或失治则可由表及里或变生危证,这种变化是有规律而循的,无论是在外感病中,还是在内伤杂病中,其规律都是有章可循的。这在张仲景的医书中及温病学中都曾多次论及。所以证候的研究不能将证候分割开来,孤立研究,也即是不能将证放在病之下来研究,即“以病统证”,而是遵循中医证候变化规律,“以证统病”来进行中医药的研究,而且研究“以证统病”是补充及完善证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3.“以证统病”的缺陷 “以证统病”的研究现在并不多。没有列为当前研究中医药工作的主流,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对于“以证统病”还是“以病统证”,当前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在新药开发上,有人认为;“以证统病”,用中医的证候包括一种或几种西医的病名,因其概念的模糊和病例数相应增多而不被看好[10]。还有的认为 [11]:且不说证的规范化问题尚没有得到解决,即便解决了单纯证的研究在如何使受试群体背景的相对一致以及试验组、对照组之间的可比性等方面仍会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有的认为[12]:“以病统证”和“以证统病”各有其特点和目的意义,“以病统证”适用于临床,“以证统病”得不出各个疾病的疗效。有的提出[13]:“以证统病”,对隐蔽的危重诸况不能阐明,对预后吉凶判断不明,缺少有效快捷的治疗手段,是否“以证统病”,值得探讨。
4.“以病统证”的缺陷
中医研究“病(西医)”的历史,自现代医学引进中国以来,已近二百年,其研究方法及缺陷值得我们总结反思。
肺结核病,中医称之为肺痨。自《素问·玉机真藏论》及《灵枢·玉版》开始就有对其症状的描述,直到元代的《十药神书》成为我国治疗肺痨现存的第一部专著,以及后来的《医学正传·劳瘵》中则明确提出杀虫与补虚两大治则,说明中医对其“病”的研究非常深入持久。可惜由于中医对其“证”本质的研究还存欠缺,以至于疗效无明显的提高,加之现代医学的异烟肼、利福平等抗结核菌药物的问世,中医治疗肺痨的这一阵地已经丧失殆尽了。
慢性病毒性肝炎,三十余年前,西医主要采取的是被动疗法——“护肝”:即休息和维生素类、肝太乐、肌苷等及对症处理,疗效不佳。而中医界则在归纳古代文献及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慢性病毒性肝炎的临床表现,辨证论治,采取疏肝理气,健脾化湿,清热利湿,活血化瘀等治法,虽然不能完全治愈,但在改善临床症状和生化指标上获得了良好的疗效,深得社会的认可。自现代医学在1963年发现了乙肝澳大利抗原后,中医界开发了以“灭澳灵”为代表的中成药,以及观察了大量的中药方剂对乙肝表面抗原的阴转研究,但结果并未取得实质性的疗效;后来的乙肝大三阳的转阴研究,中医界也作了积极的尝试,但其结果也并不满意。近年来中医界对HBVDNA的转阴的研究也无明显的进展。纵观西医的研究,近二十年来取得了飞速的进展,由于核苷类抗病毒药——拉米夫定类药物的问世,其疗效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尤其是慢性丙肝的治疗,由于长效干拢素和利巴韦林的运用,西医已号称可以治愈慢性丙肝了。目前慢性病毒性肝炎的治疗阵地的重心已被西医所控制,只是在抗肝纤维化及肝硬化上的治疗上,中医还存在着明显的优势。
当前恶性肿瘤的治疗也正在步中医治疗慢性病毒性肝炎的老路。目前中医治疗恶性肿瘤只是在治疗放、化疗后的支持疗法和防止放、化疗的毒副作用上,以及恶性肿瘤的晚期患者失去了放、化疗及手术的机会,才会找到中医。实际上中医治疗恶性肿瘤只是辅助性的治疗。
我们知道,每一门科学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中医学也同样如此。西医研究的是“病”,辨病论治;中医研究的是“证”,辨证论治。而且一个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学科,其研究对象及目的一定应当是明确的,并且其研究的对象应和其理论体系相一至,其学科才能健康快速的发展。辨证论治是中医独特的优势,是认识人体生理、病理,从而治疗疾病的工具。多年来,中医的研究却是在以“病”为主。这种将中医的“证”舍去,而研究“病”,既是舍去其长处,使用其短处。其结果是导致了中医的治疗阵地渐渐失去。这表明如果一个学科脱离自已的理论体系去作研究,那么是难以出成果的。
中医和西医治疗疾病的理念是不一样的。西医治病是针对病理的改变、生化指标的恢复、病原微生物的杀灭。其针对的是局部的病变。他实际上就象在修理一部机器,寻找(诊断)某个损坏的零部件(器官组织),或某个不通的油路(血管)和电路(神经),进行更换或修理(治疗)。而中医学是从宏观角度,强调人体是个整体,注重人体的阴阳平衡,《内经》中有“阴平阳秘,精神乃治”;“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等。自然界有生态平衡,生态平衡失调就会产生各种自然灾难。人体也有生态平衡,平衡失调,必然要产生疾病。中医诊断疾病就是辨别人体生态失衡的原因,从而治理生态失衡,既调理阴阳,使阴阳平衡,总之就是修复人体的生态平衡。
现在中医研究还大量的在以“病”为主,如:低血糖危象中医诊疗方法;慢性病毒性肝炎中医诊断及辨证分型标准等。这种建立在现代医学基础上的辨证,表面上看是在辨证论治,实际上是将西医的病,拆分成一个个证进行研究,寻找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以期提高其治疗疗效。如此研究,只能说中医在研究西医,为西医的病寻找一种治疗方法(药物),他并不能提高中医的学术水平。这种建立在西医基础上谈辨证论治,完全将中医的“证”分隔来研究,破坏了“证”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没有将人体的宏观生理和病理变化放在一个整体上来研究。
中成药的研发,现在也大多以“病”为主,传统的以“证”为治疗目标的中成药已难以寻觅。在中成药的介绍上,也是大篇幅的介绍现代药理研究的成果,以至于好似是在介绍一个西药。基本见不到“证”的研究成果。
至于同样一个“证”,有的“证”中医一时还无法治愈,我们认为中医的“证”存在“轻、重”之分[14],“重证”由于目前中医界对其认识还有限,所以一时还难于冶愈,这是今后中医界研究的重点。
西医研究治疗对象的是“病”,因此其学术组织、临床科室、学术(期刊)传媒及科研课题,始终是围绕着“病”而展开。中医是以“证”为治疗对象,辨证论治是其认识人体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的手段。因此其研究对象必定应是“证”,深入研究“证”的发生、发展规律及治疗方法,这样才能保证中医药事业的快速健康发展。可是当前中医研究“证”的学术组织有吗?研究“证”的临床专科有吗?研究“证”的学术专刊(期刊)有吗?如此“三无”[15]现象,中医的发展必定是会受到影响,这可能是导至中医界舍“证”而去研究“病”的原因之一。也说明了“证”尚未进入中医研究的主流。
要保持一个学科快速、正确的发展,其研究方法很重要,所以探讨并完善中医学术的研究方法,更正目前“以病统证”分割证的完整性研究中医的方法可从临床做起,“以证分科”,研究“证”的演变规律,从而提高“证”的疗效。
5.“以证分科”的可行性
我们知道,西医研究病,辨病论治,故其临床以病分科诊治。中医研究证,辨证论治,因此其临床分科乃应为证。目前,尚无任何中医医疗机构以证分科诊治疾病,而均参照西医学的模式,以病(西医)分科,以研究病为中心,先辨病,再辨证分型论治,将中医学的证分割于各个病之下,使之与他病的证互不关联,令证孤立起来,如此,则无法完整地对中医学的证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中医学作为一个有独立而完整理论体系的学科,其一切研究和实践都应遵循自身的理论框架,而辨证论治理论是中医理论体系的精华之一,以辨证为主体,理、法、方、药皆以证为中心。辨证求因,审因论治,为其临床工作的核心内容,最终目标是证的疗效,疗效是一个医学存在的生命线,因此证的研究就是中医的生命线。研究证的疗效就应从临床做起,以证为中心,以证分科[16],以证统病,研究中医,从而促进中医事业的发展。因此我们就此研讨了中医内科以证分科的思路。
5.1 证转变有规律性
中医学的证有其自身变化的特点和规律,《伤寒论》以“六经”传变为一个系列,温病学是以“卫气营血”传变作为一个系列。其变化是以正邪盛衰变化为主导,从而导致寒热虚实的转化。经治疗后,证可由里出表;误治或失治则可由表及里或变生危证。如:误治的传变,《伤寒论》载:“问曰:何缘得阳明病?答曰:太阳病,若发汗,若下,若利小便,此亡津液,胃中干燥,因转属阳明;不更衣,内实,大便难者,此阳明也。”白虎汤所治大热大渴的阳明经证,如高热耗伤津液、如不及时治疗,可传变为热结便秘的阳明腑证。
正因为证有其自身的传变规律及系统性,所以证的研究不能将证分割开来、孤立研究,而不能以病分科而将证放在病之下来研究。因为这种建立在病基础上的辨证,表面上看是在辨证论治,实即将西医的病拆分成一个个证进行研究,为西医的病寻找一种治疗方法,以期提高临床疗效。这种建立在西医基础上的辨证论治,完全将中医的证分隔来研究,破坏了证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没有将人体的宏观生理和病理变化放在一个整体上来研究,无法系统的、全面的观察到证的变化规律性。如此,实为中医研究西医,并不能提高中医的学术水平。所以应将研究从“病”的思路中解放出来,转移到研究“证”的思路中去。研究中医的证,可从临床做起,“以证分科”,各科合作又可全面研究证的变化规律,此乃全面而又系统研究中医的方法,可以弥补目前使用的“以病分科”的缺陷。
5.2 以证为研究单元的科学性
中医学的以证分类和西医学的以病分类,都是生物医学中的一门分类学,是一种对病、证状态进行分类的研究方法。因为西医研究病,所以西医学必然是要以病为单元分类。中医学是研究证,辨证论治是其主要工作内容,因此以证分类研究就是其自然归属。
历代以来中医学就有以证分类研究的内容,如:八纲辨证、脏腑辨证、经络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以及病因(六淫、疫疠等)病性(气、血、津液)辨证等,在上述各个不同分类的方法下进行中医的研究工作,因为他符合中医学的辨证论治的思维过程。实践证明他们成功的分类研究,对当时的中医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卫气营血证及三焦辨证的分类研究,科学的体现了温病的发生、发展过程及治疗转归,其研究成果构成了温病学的辨证施治的完整理论及实践体系,他成就了中医温病学,其科学性已得到中医界的认可。《伤寒论》是以六经分证研究,其科学性、实用性得到中医界的崇拜,并获得了国际上的认可。而研究杂病的专著《金匮要略》,其分类是以病机相同、证候相似或病位相近者来归类研究,这种研究方法仍然在现代中医科研中使用,但未能成为当前研究的主流,而是被研究“病”所取代。
在同一理论指导下,外感(伤寒、温病)病有其证的变化规律,能够以证分类研究,其科学性、实用性,已得到中医学界的公认。内科杂病的证也同样能够以证分类研究,并也应有其变化规律,只不过是人们现在还未将其分类(科)研究,因此也就无法总结出他的变化规律。因此以证为单元研究证是有其临床科学实践基础的。
目前以证为单元的研究专著有不少:如:《血虚证辨治与研究》(陈如泉主编,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0年8月第一版),他系统地论述了血虚证的发生、发展、传变规律,讨论了血虚证的诊断及治疗和血虚证与现代医学的关系。这为以血虚证为单元的研究作了科学的理论准备。
5.3 以证分科的必要性
医学分类,是知识的增加和积累所需。当对疾病的诊治掌握了一定的规律时,要求逐步地将它们分门别类来研究,对疾病的知识掌握得越多,分类也就越细,以更好地促进其学科的发展。而要保持一个学科快速、正确的发展,并保持其学术特色,需要把其研究对象放在统领位置,才能使其保持自主发展的势头。西医学就是将其病放在首要位置,因此其学科发展迅猛。反观近几十年来,中医学的大部分研究是停留在将西医的研究方法套用在中医上,“以病分科”、“以病统证”,使得中医学的发展并没有发生质的飞跃。
我们提出“以证分科”,有助于研究证的演变及发展转归,更深入地认识证,以提高临床辨证水平,对指导临床治疗有着重要的意义。研究证的变化规律,可预测证的预后,掌握治疗的主动权,提高证的疗效,补充及完善证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学作为一个有独立理论及实践体系的学科,必须建立自身的研究体系。因此,探讨并完善中医药学术的研究方法,更正目前“以病分科”而分割证的系统性的错误,提出新的研究模式,探索一个完全符合中医学辨证论治思维并遵循中医学证的变化规律,即“以证分科”、“以证统病”以证为统领的方法来进行中医学的研究,这是当前中医药研究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也是今后中医药发展的突破口。同时,以证分科可利于突出中医的护理特色,笔者在临床观察到:纵在夏季,阳虚病友仍喜温,惧怕冷空调;而阴虚火旺者喜好冷空调,此两类病友分住同一个病室,常因冷空调的开或关而闹矛盾。在冬季两者又因暖空调的温度高低,而产生不愉快。如果以证分科,这一问题可迎刃而解。
5.4 以证分科的方法思路
目前,中医学尚无统一的、规范化的、方便临床运用的分类方案。对于传统中医证的分类方法,有的过于简单而笼统,如:八纲辨证、三焦辨证;有的太繁琐,如:脏腑辨证。用于临床分科并不完全实用。因此,必须研究新的证候分类方法,以适合临床使用。
我们建议拟采用现行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本科教材《方剂学》(谢鸣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版)相对应的分类方法对证进行分类,每一大类可根据需要再分若干个子类,确立临床以证分科的框架。其理由有:①分类明确,简而不繁琐,因而临床使用方便;②方证对应,对今后有利于研究推荐疗效突出的方药,提高中医药的疗效水平;而且方证对应是目前研究比较活跃的领域,有利于推广使用;③研究提高方证对应的疗效是当前中医研究的迫切需要。
为方便临床运用及根据各级医院的需要,可根据证的分类结构,将其分为一级专科或二级专科。如在实践中发现《方剂学》的相对应的分类方法有不适合临床证的分类,可参考八纲辨证、脏腑辨证、经络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以及病因(六淫、疫疠等)病性(气、血、津液)辨证等,选择适合临床运用的证的分类法来补充,取各证的分类方法优点,其原则是切合临床实用。
5.5 以证分科的可行性
在以证统病的实践过程中,要求中医临床医师具有西医全科医生的水平,能基本处理西医常见病的诊治和预后,这一点是可行的,如各级综合性医院的中医科病房(中西医结合科病房)现已完全能做到,在中医医院也同样是可以做到的。临床中,西医有大内科,病友在大内科初诊后,分流到各专科诊治,同样中医内科也可采用这种方法,进行以证分科,以证统病,从临床实践来看也是可行的。
5.6 相似、相兼、错杂证及证变化的处理
对于相似证,并列为一类。而相兼证、错杂证的处理,是找主要矛盾,以何证为主,归属何证。现代医学也是这样处理,如有的病友同时患有高血压病、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分属三个系统的病,其住院根据当前以何种病为主要矛盾时而按排在相应科室就诊。如果对于有的证一时难于分类的,可与相近的证归并研究,等条件成熟后再行分类。现代医学也有这种现象,如:风湿性疾病,既往多归内分泌科,也有归骨科,现有的单独分科研究;痛风,有的归内分泌科,也有归骨科,也有的归风湿科;骨质疏松症,既往多归内分泌科,也有归骨科,现有的单独分科研究。
而证是动态变化的,不管是正治,还是失治、误治,都有其变化规律性,这在张仲景的医书中有多处论述。临床处理的原则是,证转变时可请相关科室会诊或转科治疗。中医是辨证论治,治疗的是证,追求的是证的疗效。如此,既方便集中力量攻克各个证的疗效,又可促使各科室合作以研究证的变化规律。
5.7 与中西医结合的关系
临床工作不但要提高证的疗效,也要研究提高病的疗效,因此要注意研究证与病的诊断关系和证与病的疗效关系[17]以及治疗用药时证与病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8];不但要研究宏观的证,还要研究微观证,以及宏观证与微观证的关系,便于中医与现代医学共同发展。
6 结语
中医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辨证论治是其诊治疾病的主要手段,是以提高证的疗效为最终目的,而疗效是一个医学学科存在的生命线,因此一切研究应围绕着证而展开。目前临床实践,将中医的证分散在西医的各个病之下来研究,割裂了证的完整性,没有考虑证的演变规律,不符合中医认识病证和诊治病证的思路,必然影响到中医学的发展。而“以证统病”、“以证分科”,是充分按中医辨证论治的思路,以证为研究单元,研究证的发生、发展演变规律以及治疗后的转归,进而探讨证与病的关系,包括证与病的疗效关系、诊断关系等。基于此,我们提出了目前尚未有的“以证分科”、“以证统病”的研究方法、内容和措施,以期建立“以证统病”的临床科室,为中医研究探索一个完全符合中医辨证论治的思维,以证为统领的研究中医学的方法。以期为建立中医学自身的实践研究体系,建立“以证分科”、“以证统病”的新型中医临床科室,做好理论准备。
参考文献
1 杨宇飞̣۪.从证候的普适性和基因角度入手开展证候研究[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02,22(6):410—411
2 洪净. 中医辨证的思维模式和方法研究[J]. 中医杂志,2003,44(1):8—10
3 陈伟. “中西医结合”与“病证结合” [J].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1998,15(2):139—142
4 尹天雷, 乔铁, 刘天舒等. 热炎宁颗粒治疗风热证148例临床观察及中医“以证统病”的临床科研思路探讨[J]. 中国医药导报,2009,6(11):20—22
5邱伯梅,陶克文.治疗老年脑病经验[J].实用中医药杂志,2008,24(1):44—45
6 李攻戍∙ 从技术评价角度思考中药新药的临床优势与特色[J].中国新药杂志,2008,17(1)86—96
7郭振球. “主诉辨证治法”以证统病[J].天津中医药大学学报,2009,28(1)1—3
8王放,焦一鸣,汤萍.谈病证的个性与共性在临床中的运用[J].中医药学报, 2009,37:(3)4—6
9 巩琪,栾杰男,郑大为,等.刍议中医临床辨证论治[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5,11(3):174—175
10 张瑞明,李廷谦. 中药新药Ⅱ、Ⅲ期临床研究有关问题的探讨[J].中药新药与临床药理,2004,15(1):66—67,
11王海南.中药新药临床试验的特点和难点[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07,27(7)650—652
12 危北海,刘薇,苑惠清. 构建中医临床疗效评价体系的探讨[J].天津中医药,2006,23(5)353—357
13 张耀坤. 中医临床误诊病例分析[J]. 实用中医内科杂志,1998,12(4)11—12
14焦一鸣.王 放.再论辨证论治的不足与完善[J]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10(7):16—17
15焦一鸣. 王 放. 中医证的研究处于三无状态[N]. 健康报,2011-1-5(5)
16焦一鸣. 王 放.汤 平.证候研究方法简述[J]. 中医文献杂志,2010;28(6):26-28
17王 放. 焦一鸣.汤 平. “证”研究的现状及思路[J].中医研究,2010;23(9):6—8